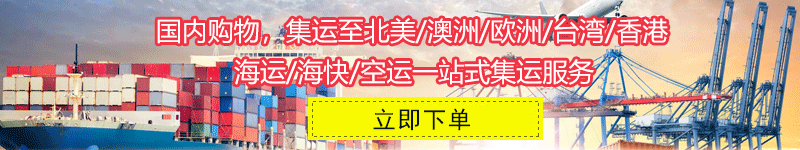文|周松芳,文史学者
欧洲国家里,英国人的饮食就像英国人的言行一样刻板无味。
林语堂先生曾对英国的饮食大加贬损:
英国人不郑重其事地对待饮食,而把它看作一件随随便便的事情,这种危险的态度可以在他们的国民生活中找到证据。如果他们知道食物的滋味,他们语言中就会有表达这一含义的词语,英语中原本没有“cuisine”(烹饪)一词,他们只有“cooking”(烧煮);他们原本没有恰当的词语去称呼“chef”(厨师),而是直截了当称之为“cook”(伙夫);他们原本也不说“menu”(菜肴),只是称之为“dishes”(盘装菜);他们原本也没有一个词语可以用来称呼“gourmet”(美食家),就不客气地用童谣里的话称之为“Greedy Gut”(贪吃的肚子)。事实上,英国人并不承认他们自己有胃。……英国人感兴趣的,是怎样保持身体的健康与结实,比如多吃点保卫尔(Bovril)牛肉汁,从而抵抗感冒的侵袭,并节省医药费。(林语堂《中国人》,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325页)
曾任“中央日报”驻伦敦特派员的名记徐钟佩也说:“英国根本无所谓烹调,随便什么蔬菜都是拿来白煮,我常说在英国当厨司要算天下最容易的职业,凡到过英国者,都知道英国菜的单独乏味。”(《中央日报周刊》1948年第5期)
广东人把中餐带入英国
或许正因为英国饮食文化的不彰,使中华饮食得以“乘虚而入”,写下可观的篇章;主要功劳,应归于广东人。由于一口通商的关系,广东人很早就践土英伦。
据我们中山大学程美宝教授考证,早在1769年8月广州有一位陶塑匠搭船去到英国,受到热烈欢迎。稍后,又有一位名译Whang Tong的人曾在1775年到访伦敦,并与英国的文士和科学家会面,还极有可能见过当时的英国皇家学会主席班克斯。当然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小人物。(《“Whang Tong”的故事——— 在域外捡拾普通人的历史》,《史林》2003年第2期,第106-116页)
再晚一点,1816年,冯亚生、冯亚学两个广东商人因其伯父任广东海关税收官,出于好奇搭船赴英伦,后赴德国,登台表演二胡,受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接见并委托进入哈勒大学协助德国汉学创始人之一威廉·夏特研究汉语。(李明欢《欧洲华侨华人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版,第70页)
到了鸦片战争后,国门被冲开,去英国的广东人就更多了,除了水手外,震惊于西洋人以船坚利炮为象征的先进科学技术,像晚清的一代重臣张之洞在《劝学篇》就提出:“出洋一年,胜读西书四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三年”,因此求学留洋者也越来越多。
在朝廷派遣官费留学生之前,不少广东人因地利之便及认识之先,早就私自留学英国了。王韬1868年漫游至英国时,就写到他与留学生韦宝珊、黄咏清一同出游的情形。(《漫游随录》,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30页)
1873年,广东新会人伍廷芳(秩庸)自费留英,并考取律师资格。1876年郭嵩焘出使英国时,曾欲努力罗致麾下做译员或随员,而伍氏颇有不屑,旋任清廷驻美领事。这在郭嵩焘的《伦敦与巴黎日记》及随使的广东人刘锡鸿的《英轺私记》中均有记载。
延至20世纪初叶,在欧洲各主要港口城市,相继出现了一批由华人开办的、或以接待华人为主的旅店、客栈,即相关英文史料中的“chinese boardinghouse”,荷兰文史料中的“chineezenlogement”,称为“华人水手馆”,也有称“行船馆”的。因此,哪里有港口,哪里就有“华人水手馆”。在阿姆斯特丹,自1912年开设第一家水手馆后,不到10年即增加10余家,至1933年,又增至29家。在英国,则集中在港口城市利物浦等地(李明欢《欧洲华侨华人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版,第169-P170页)
在18世纪,少数中国船员即来到伦敦东部,到19世纪,小规模的中国社团在伦敦、利物浦、格拉斯哥和加的夫等地相继建立。到19世纪80年代末,毗邻西印度码头的伦敦莱姆豪斯区已出现了中国杂货铺、餐馆和会所。在利物浦,一个相对较大的中国社区在匹特大街及邻街建立起来了,还开设了店铺和小吃店。只是这些餐馆和小吃店主要服务中国船员、船坞工人和学生,没有记录表明有西方顾客光顾过这些餐馆,所以后来讨论英国中餐的起源时,往往被人忽略。(参见约翰·安东尼·乔治·罗伯茨著,杨东平译《东食西渐:西方人眼中的中国饮食文化》,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版,第108页)
英国中餐馆这种草根出身,初期的不待见,反而,使其葆持相对的地道。徐钟佩有观察说:“论烹饪,巴黎的中国馆子比伦敦的好,论风味,却是伦敦的比巴黎的道地,巴黎中国馆子,座位都依法国沙龙式,倚墙而设,和菜蔬俱来的,又常是一碟面包,总脱不了洋味。伦敦中国馆子多半是中外分坐,入席以后,四顾全是同胞,依稀身在故国,只有在瞥见侍者身上的一套燕尾服,才恍然是在多礼的伦敦。”(徐钟佩《伦敦和我·中国菜馆》,选自《中央日报周刊》1948年第5期)
辛亥革命开辟中餐馆新时代
辛亥革命,华侨助力甚多;革命胜利,华侨民气一新,旅居海外者日众。故时人谓:“自1912年至1920年为华侨留英最发达之时期。华侨多居伦敦、利物浦、加尔的弗(CARDIFF),次为STAFFSWINDONBRISTOL,当时华侨人数,约一万左右;工界约占百分之九十,学界商界仅占百分之十而已。”许多中餐馆便渐次开了出来。
但是好景不长,十年之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欧洲经济凋敝,工作机会减少,后又发生第一次全球经济危机,所以“华侨之人数,日渐减少”。(《华侨半月刊》1932年第6期莫耀《旅英华侨杂述》第27页)。邹韬奋1933年的访英观察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十年前,旅英的华侨至少在一万人以上(听说在世界大战时达一万五千人),但是最近已减到三千人左右了。在英的华侨,大多数在轮船上做水手或火夫,这种苦工作,在经济繁荣时代的英国人多不愿干,所以肯吃苦的‘支那人’要得到这样的机会并不难。”因而“旅英的华侨以伦敦及利物浦两地为最多。在利物浦的约有三百八十人,其中约一百八十人是水手和火夫,其余除少数小商人外(开杂货店),多业洗衣作,在前面‘利物浦’一节中已略有述及。在伦敦的约有四百五十余人,可算是在英华侨的大本营。其中有两百人是水手和火夫,失业者已达一百五十人;在中国菜馆(伦敦有四家)做厨子或侍者等有百人左右,在英国菜馆当厨子或侍者等,原也有百人,现在失业的也有四十人了;此外在东伦敦开让商店做中国人生意的约有五十人。”
伦敦的中国菜馆集中在东伦敦边上的中国城。邹韬奋说,所谓“中国城”,不过有几街里面中国人特别多些罢了。“记者到东伦敦去观光时,也到侨胞麜集的区域去看看,差不多都是广东人;最显著的是中国药材铺、中国杂货店,里面有种种中国的土货”。(《萍踪寄语·英国的华侨》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45-146页)
由于广东人开辟的历史,以及后来英国人与香港的特殊关系,以至有些英国人把广东话当成了中国话。民国的风流人物,曾任国民党中宣部长,也是徐悲鸿第一任妻子蒋碧微长期的情人的张道藩的一则轶事,颇资说明。
1919年11月下旬,张道藩与四十位从上海启程赴法勤工俭学,船上每周一次演讲,一次一位在广东传教多年的英国牧师用纯熟的广东话作传教性演讲,发现有人不专心听,事后才知,许多人不懂广东话,而他把广东话当做中国的国语了。他们一行在得知战后经济萧条,法国无工可勤,其中七八人便转往英国。1920年1月9日到达伦敦提尔布勒码头,张道藩的老同学石瑛、吴筱朋、黄国梁、任凯便领带他们乘火车抵达伦敦市中心区,带到一家广东人开的中国楼饭馆——— 颇有才到英国,又入广东的味道。(《传记文学》1962年11月第1卷第6期张道藩《酸甜苦辣的回忆》第40-41页)
而最有“广东情怀”的,既不是居英的中国人,也不是旅英的中国人,而是一个地道的英国人——— 著名汉学家哈罗德·阿克顿(1904-1994;又译作艾克敦)。艾克敦祖上为意大利贵族,母亲为美国大亨之女,家产丰厚。此公先在法国呆了几年,吃惯了法国大菜,回到了英国后,再也吃不惯英国饮食了。怎么办?他想到了广东菜。“于是他雇了一个曾在温伯利一家中餐馆工作过的广州人宋重做自己的厨师。宋重随身带来了中国的餐具和一小罐茶叶、金橘、一罐姜粉、数量惊人的小袋大米、粉条、荔枝、蘑菇和名贵草药、干货等食材。事实证明,宋重还能启发阿克顿的诗歌创作灵感,因为他做的饭菜味道一次比一次好。……阿克顿说道:‘我希望自己能成为完整的中国人。’宋重去世后,阿克顿在哀悼亡友时说:‘那古老文明孕育出的出色的烹饪法不光能满足人们的食欲,而且还能启发人的智力。’”(《东食西渐:西方人眼中的中国饮食文化》,第122页)
杏花楼——伦敦最老的中餐馆
华人初到英国的情形,与初到美国差不多,多单身无家,吃饭的问题不得不靠自己人开小饭馆解决。故唐人街内的小饭馆,便一直相对正宗而地道。唐人街或华人聚居地在伦敦东区,东区是没有大的中餐馆的;反之,在相对高大上的伦敦西区的中餐馆,则仿佛美国版的豪华杂碎馆。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人访英,所见仍是如此:“中国饭馆在伦敦者有大者三四家,小者则须求之于唐人街。唐人街者,中国水手麇集之区也。其地污秽不堪,药店杂货店,应有尽有。而饭馆之菜肴,则较饶中国味,因为此地之中国饭馆,始系真为中国人而设者也。”(《现代学生》1933年2卷6期余自明《英国留学生活之断片录》)
也许最初的小中餐馆,就像合伙做饭了一般,不名于外,因此史家考证说,“第一家正式的中餐馆开设于1908年,位于东伦敦中国人的聚居区。随后几年又陆陆续续在同一地区开张了三、五家,它们均面向中国船员为主,规模很小,而且十分简陋。到二三十年代时,在伦敦约有十数家此类低档次的中餐馆,其服务对象主要是当时在英国求学的中国留学生,以及少数属于英国社会下层的工人。”(李明欢《欧洲华侨华人史》,第195页)当然临时的中餐馆则起源更早:“伦敦最早的中餐馆,可追溯到1884年英国伦敦举办为期半年的养生会上,中国开办临时的‘紫气轩’中餐馆。”(同前书,第190页)
“紫气轩”中餐馆,其实大有来头;它是由自1863年起即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长达45年之久的英国人赫德(1835-1911)一手促成的;展台的布置、食材的供应、厨师的雇佣等都由他亲自安排。目的是要提升中餐馆的形象,改变英人的偏见,努力使其为主流的英国人所接受。
真正扭转这种局面,得等到广东人开的杏花楼出来。华五(郭子雄)先生在《宇宙风》1935年第1期撰文《伦敦素描·中国饭馆》:“牛津街最华贵的杏花楼,本是伦敦的第一家中国饭馆,雇主几全为外人,穷学生是不大去得起的。一九二九年的冬季,听说杏花楼老板被人告发贩卖鸦片烟及作其他不正当营业,警察厅强迫他关门,单是房金一项损失便有一万八千镑。一时中国同学们都叹气,觉得这样大一家饭馆倒闭的可惜。终于因为知道杏花楼的人不多,现今走过牛津待的同学能有几个指出当年杏花楼的所在?”这杏花楼老板,当是邹韬奋所说的张朝:“华侨中开菜馆的已算是顶括括的阔人了!东伦敦华侨里面有一位名张朝的,在伦敦开了三十年的菜馆,现在算是东伦敦华侨的‘拿摩温’(NUMBERONE,第一号)的领袖。”(《萍踪寄语·英国的华侨》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46页)说杏花楼是伦敦最老的中餐馆,也是说得过去的。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