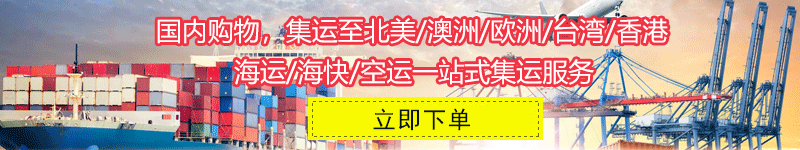【写在前面的话】
富平安(Anne Swann Goodrich)是我们的母亲。她希望读者能够了解,在美国,有很多人非常敬佩中国人民和他们的成就。母亲的整个人生,都在讲述她对中国及其历史和民众的热爱和兴趣。她一直希望能在她的丈夫(中国历史学教授富路特L. Carrington Goodrich博士)退休后,与他一起回到中国去生活。尽管未能如愿,她还是怀着这样的心意,在1980年代两次回到中国,一次是和丈夫一起,一次是在丈夫故世后,她带着一个大家族回访了中国。她出版的著作,旨在增强读者对中国文化的欣赏;她也热切地为所有对中国感兴趣的人们宣讲中国,为学校里的孩子,向教堂里的教友,甚至专门回应前来咨询的记者们和学者们。102岁的时候,她做了最后一次演讲《中国对西方的贡献》。我们希望她的自传的发表,能够对中美关系的改善有所助益。
哈伯德·卡林顿·古德里奇(Hubbard C. Goodrich)和安·古德里奇·琼斯(Anne G. Jones)
2020年5月7日母亲节前夕,时年88岁,于美国缅因州
小引
尽管过去一些年也写过一些经历,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把我的一生给记下来。但我还是被鼓励着去回忆一些重大的事件和想法,包括我生命中的那些里程碑。也许是因为我到了107岁的年纪(译者注:传主Anne Swann Goodrich,1895-2005,此回忆录写于2002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新近见到的档案显示,她的中文名字写作“富平安”,本文采用她的中文名。之前有根据音译称她作为安·丝婉·富善、安·斯旺·古德里奇,她也常被称为“富路特夫人”或者“傅路德夫人”),毕竟经历了毋庸置疑的最有趣的一生。我要在一位友人的帮助下,把这件事给承担下来。对于我所经历的整整107年而言,这显然只能是一份缩略的短章罢了。
我的大家族
我的原籍是英国,这大概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早期。移居到美国的祖辈,最初是从佛吉尼亚州的詹姆斯敦(译者注:Jamestown,是英国在美洲的第一个永久殖民地,建于1607年,是美国现代史的发源地)登陆的。几年以前,我们故地重游,还专门去了北卡罗来纳州斯旺角(Swann’s Point)的种植园(译者注:佛吉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现在是美国东海岸南北相邻的两个州)。托马斯·斯旺(译者注:COL Thomas Swann, 1616-1680)的老墓还在那里,他是1680年去世的,上面有家族徽印。那一时期家族故人的坟墓,我们就只找到了这独一个。我的八位曾祖父母都在1790年到1810年间,出生在美国。(图1)
图1:富平安的先辈托马斯·斯旺的墓碑。2013年3月Joseph Sullivan摄影,源自https://www.findagrave.com/memorial/6126891/thomas-swann。
我的祖父是塞缪尔·阿什·斯旺(Samuel Ashe Swann),祖母叫玛莎· 罗莎莉·特拉弗斯·斯旺(Martha Rosalie Travers Swann),他们于1859年在佛罗里达州拿骚(Nassau)县的费南迪纳(Fernandina)市结婚,分别活到了77岁和43岁。外祖父叫丹尼尔·帕金斯·斯密斯(Daniel Perkins Smith),外祖母叫克妮莉娅·卡罗丽娜·克里斯提娜·霍普金斯·斯密斯(Cornelia Carolina Christina Hopkins Smith),1861年6月2日他们在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维尔结婚,分别活到了73岁和70岁。
我的父母我能说什么呢?他们都出生于佛罗里达。我的父亲,塞缪尔·大卫·斯旺(Samuel Davis Swann),1864年8月17日出生在佛罗里达州阿拉楚阿(Alachua)县的盖恩斯维尔(Gainesville)。我的母亲法朗西斯·斯密斯(Francis Smith)1868年3月14日出生于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维尔(Jacksonville)。他们约在1886年在杰克逊维尔结婚,结婚的时候还很年轻,差不多22岁和18岁这样吧。父亲是一名药剂师,母亲除了为教堂做点事情外,没有出外工作,这在当时是蛮典型的。1895年7月4日我,安·帕金斯·斯旺(Anne Perkins Swann)出生在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县的费尔南迪纳海滩(Fernandina Beach),就是现在的阿米莉亚(Amelia)岛。所以,我的根在佛罗里达。我的名字是随我的大姨(译者注:Anne Perkins)来的,“安”也是我曾外婆的名字;我的中间名“帕金斯”是随的我外公。我一直喜欢我的名字,安,在汉语里是“平安”的意思(图2)。
图2:2岁时的富平安。
1907年4月1日,我母亲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罗兰(Roland)公园去世。她刚到39岁,而我还不到12岁。我想我的母亲也许是能够得到的最好的母亲吧,实事求是地说,我就从来没有从她的离去中缓过来神来。我的父亲1910年1月1日在他45岁时去世,我才14岁。父母离世后,我跟着亲戚过。有时候是住在从政的大伯(译者注:Edward Swann)家,有时候是住在新泽西的极善交际的大姨家。我是极为幸运的,伯父和姨妈都很关心我,帮助我度过这些困境并长大成人。但是,我不得不说,做孤儿,真是个沉重的心理负担。(图3)
图3:1907年,富平安快12岁时,母亲去世。
我人生的一些重大日子看上去有些奇特。我常常念及我母亲是早逝于4月1日的,我更记得父亲是在1月1日过世的。我自己的生日则是在7月4日,我不是说这会令我更爱国,但小时候会让我感觉自己很重要,全国人民都为我祝贺生日呢。
我活过了一百岁,这看起来非同寻常,因为长寿并不是我们家族的特征。按照今天的标准,我的父母去世的时候都太年轻了,我母亲才39岁,而父亲也不过46岁。我的外公在我出生前6个月就去世了,时年73岁;而我的爷爷77岁就过世了。我非常惊讶,我怎么活了这么长,而且还不明就里。我曾想能活过70岁就很了不起了呢,但可能与我父亲自己配方的“万宝急救药”有关,他是药剂师嘛。我是吃着它长大的,我只要一生病就吃这个药,而且一吃就好。
我试着去回想最早的记忆,能想起的是四岁我们一家住在华盛顿的时候。我有一个哥哥,叫多诺万(译者注:Donovan Swann Sr.)。他去上学的时候,有一次在健身房里受了伤,病情危急。我妈有个闺蜜来照顾我,这样我妈就能把全部的时间放在我哥身上。我过去常说,尽管我哥比我大七岁,我记得的倒是我推着婴儿车,把我哥摇来摇去的。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开过侦察机。在他家客厅的门上,很多年都挂着他执飞过的一架飞机的螺旋桨。他也是最早从水上开起“水上飞机”的人之一。他最初的职业是一名蚀刻师,可他也是一名音乐家,他给孩子们写乐谱,但是从没发表过。有一段时间他做过巴尔的摩歌剧公司的经理。他的所有活动,我过去都常常介入一点点;但我不记得他去世的具体时间了,我只能回忆起他只活了四十几岁。
学生时代
我真的记不得我最初的校园时光了。但是我确实记得我在巴尔的摩上过幼儿园,我们串过小珠子。至于小学,我记得是在一个叫“罗兰公园”的小学上过一年级,而我在那儿很不开心,我非常讨厌那个地方。不得已,我的父母把我领出来,送到天主教修道院,我太爱那个地方了。单说一件事情,就让我喜爱那些个修女和神父——他们常常出来和我们一起玩耍啊。我爱去小教堂,什么都爱!我的上帝啊,每节课前我们都要祷告,每节后还要再祷告,我的祷告经验就是从那里入门的。我真是非常喜欢那所学校,老师们都很和善——有些古板,但是很和善。我记得童年时我喜欢爬树,坐在树丫上读书。《小妇人(Little Women)》是我最爱的书,但是我喜欢爬树胜于喜欢读书。
我母亲去世后,她的姐姐安把我带到她家,我的名字就是由她而来的。她是个聪明人。她把我送到位于新泽西州普兰菲尔德市(Plainfield)的哈德里奇寄宿学校(译者注:The Hartridge School,是创建于1884年的私立女校,该校后来并校为今天的沃德罗-哈德里奇学校/The Wordlaw-Hartridge School)。我挺喜欢那个学校,我至今还喜欢。我就是在那里接受的中学教育。我的大姨就住在普兰菲尔德,所以我是可以想去就去的。但是我从来都没这么做,我太喜欢那所学校了。实际上,我从未上过公立学校。那时候,在学校以外,女性几乎没有机会参与到体育活动中去。我13岁时候开始尝试打高尔夫球,但打丢了太多球我也就放弃了。高中时我一直参加体育活动,我不算好学生,但我爱运动,这是我希望去大学的原因。我在那所寄宿学校四年,直到毕业。那所学校太棒了,毕业生都很容易被大学录取。(图4)
图4:1910年,中学时代的富平安。
父母早逝对我有什么影响呢?孤儿的生活是与众不同的。尽管我的大姨安承诺担当起已逝父母的责任,我还是不得不要学会为我自己的生活负责。她把我带到她家,告诉我怎么行事、怎么穿衣、怎么思考。但我并不总是按照她希望我的那样去做去想。她对我很好,但是我们的想法并不一致。她对着装和社交更感兴趣,我对那些提不起精神。到了大学,我才觉得我总算可以自己管自己了。
中学毕业以后,我去瓦萨学院(译者注:Vassar College,1861年作为女子学院创立,历史上曾是常春藤盟校的姐妹机构,1969年开始实行男女同校。该校早期与信奉新教的美国社会精英家庭关系紧密。富平安于1912年入校)又学习了四年,我的重点专业是美国历史。我学得非常努力才维持了平均“良上”的成绩,但是,我参与了能参加的每一项体育活动,从体操到垒球,但我的姨妈认为那不是女士应该做的事情。在那里我打曲棍球、篮球,还踢足球;我还在瓦萨赢过一次跳远比赛,我们穿肥大的黑色灯笼裤和上装。我们也玩别的,比如像垒球,我总是借我的堂兄的垒球服穿;我也玩对撞式橄榄球,运动装都是整套搭配着的呢。但只有运动的时候才能穿,在校园的其他地方被看到穿成这样,会被看作是过于狂傲不羁的表现。我对观看体育比赛没啥兴趣,让我兴起的是真的去运动起来。我计划读个体育教育的学位,主修曲棍球,可是我太会运动了,没有多少可学的呀!(图5)
图5:1912年至1917年富平安入读纽约州的瓦萨学院。左:在校园中,右:在毕业典礼上。
在瓦萨,我参演过一次我的同学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译者注:Edna St. Vincent Millay,1892-1950,美国现代抒情诗人、剧作家,1923年获普利策诗歌奖)为世界和平而写的诗歌朗诵;我第一次听说了哈里·爱默生·弗斯迪克(译者注:Harry Emerson Fosdick,1878-1969,基督教牧师、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新教内部基要主义和现代主义之争中的焦点人物。他有诸多传播甚广的布道和著作,富平安大学期间能读到的主要有1913年版的《神的人格/The manhood of the Master》和1917年版的《信仰的意义/The Meaning of Faith》等),他在那一地区传教,我读了他的书,他对我的一生影响甚大。
1917年,我从瓦萨学院毕了业。瓦萨之后,我去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译者注:Columbia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私立常春藤联盟研究型大学,创立于1754年,1896年迁至曼哈顿上城现址)的教育学院。开始的时候我修读体育教育,但后来发现不及我对基督教育的兴趣大。我就综合两者,但都没学进去多少。我从教育学院获得了硕士,尽管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颁发学位给我!我去了我想去的大学,而且我如愿以偿地得到了教师学院的学位。为了学位,我还在联合神学院修读了课程,包括最后几年在联合神学院的夏季课程。虽然我是可能从联合神学院得到一个学位的,但我傻乎乎地没有要。我做了该做的功课,但我没有得到学分。我很遗憾我没有要。我记得在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的硕士学位后,我第一年工作的所得税交的是3美金。(图6)
图6:1917年,富平安从瓦萨学院毕业时的学籍卡。已过保密期限,可以公开,成绩部分经过了隐私处理。上面填写的是她的婚前姓名,监护人写的是她的大伯(Edward Swann),家庭地址写的是在新泽西州的大姨家的住址。由瓦萨学院图书馆档案与特藏部复制并授权使用。
到中国去做传教士
过去很长时间,我都盼望着从事传教工作;而且我想去中国,到底为了啥我也不知道。我尝试着去印度,还有一些其他的地区,那时候在美国公理会(American Board of the Congregational Church)名单里有的,我都写过申请信。但其实,我对那些地方不是那么提得起兴趣。然而,公理会没有录用我,我后来去了圣公会教堂(Episcopal Church),事情才有了转机。我去了圣公会教堂,我们都确认我当时并不是圣公会的教友!我那时候就说圣公会就是我的教会就好了嘛,可是我说了“不是”。我原本只是想看看他们会不会要我,后来我倒是成了那里的教友了。
公理会对圣公会的态度一般是很迁就的,这是他们现代精神的标志。我也就被公理会差会(Congregational Mission Board)给录用了,原因只有一条,就是弗斯迪克博士给我写了个条子,说“你们如果能要她,就要了她吧”。(图7)
图7:1930年10月6日出版的《时代》杂志封面上的福斯迪克牧师像。图片已入公有领域。
当我的家人得知我想去中国做传教士,这对我那有世俗之见的大姨是个打击,她觉得这太危险了,而且是对长相和教育的浪费。因为那时我都25岁了,也许我大姨对我还能得体地嫁出去都已经绝望了。不管怎么说,我姨觉得这个想法不好,而且坚决反对,倒是另一位伯母(译者注:Elizabeth Swann)同情我的志向。而且,我觉得家人害怕我去中国,义和团(Boxer Rebellion)也是一个特别的考量。
因为我想去中国当传教士,我的家人反对;我就去我上过的中学,找了老校长。她的建议是我等到25岁,那样我就能明确我想要干什么了。于是,我就一直在曼哈顿的第一长老会教堂(译者注:First Presbyterian Church,俗称“元老教堂/old first”,建于1716年,1846年搬至格林威治村今址。1918年至1924年,弗斯迪克被任命为该教堂牧师)做事,直到25岁我去了中国。我在教堂的主要工作是组建一支女子篮球队。哦不,我从未成为过篮球队的核心人物,我最高也就长到过五英尺四(译者注,约1.63米)。另外,我当然也教主日学,我倒是把它发展了起来,而且越办越大。
我在纽约市第一长老会教堂工作的时候,哈里·爱默生·弗斯迪克是那里的牧师(译者注:富平安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曾修读过弗斯迪克牧师在哥伦比亚大学联合神学院开设的课程,并在为长老会教堂工作的一两年间与弗斯迪克牧师有过频繁接触)。后来,位于费城的长老会总会在他们的年度大会上通过决议并得出结论,认为弗斯迪克博士由于过于现代而不能再在任何长老会教堂传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对长老会无比愤怒(译者注: 1922年弗斯迪克在第一长老会教堂讲道《基要主义会赢吗?/Shall the Fundamentalists Win?》,引发论战。他反对生搬《圣经》,倡导将基督教的历史视作进步和变革的过程。1923年美国长老会全国大会责令对其言论进行调查。1924年弗斯迪克经辩护人辩护逃脱责罚,并于当年辞去第一长老会教堂牧师一职)。弗斯迪克博士原本是浸信会(Baptists)的,但最终不论是对浸信会还是对长老会而言,他都太“自由化”了。后来,就是为了弗斯迪克博士,小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译者注:John D. Rockefeller Jr.,1874-1960,美国金融家和慈善家)特意建造了 “河边教堂”(译者注:Riverside Church,是依据洛克菲勒和弗斯迪克的倡议,在纽约市上城建造的一座跨教派的面向所有基督徒的大型教堂。1930年建成后,弗斯迪克成为首任牧师,至1946年退休。另,1986年9月21日,富路特教授的葬礼弥撒也在这座教堂举行)。周日一早,等待进入河边教堂参加礼拜的人要排过两个街口。
当我被美国公理会海外传道部(译者注:American Board for Congregational Foreign Missions,后来叫做联合差会United Board)派往中国时,我满脑子兴奋,想象着北京一定是世界上最迷人的城市。(图8)
图8:1920年富平安乘坐这艘名为“亚洲皇后”(Empress of Asia)的远洋轮前往中国。
在开始讲述我的传教士生涯之前,我必须承认我觉得我是个很糟糕的传教士。我原本是要在女子高中教英文的,而且我也努力过了,但我觉得我做得并不好。好在他们给了我另外一份工作。“西德尼·甘博”(译者注:Sidney David Gamble,1890-1968,美国社会学家,创办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于1921年出版《北京的社会调查/Peking: A Social Survey》。1931年至1932年第4次来华进行社会调研时曾寄宿在富平安在北京的家)这个名字恐怕有些人都没有听说过,但他率先在中国的城镇中对北京进行了社会调查。结果显示,北京民众是贫苦的,是需要帮助的。(图9)
图9:1925年4月底,甘博(右)与富平安的丈夫富路特(中)、友人恒慕义(Arthur William Hummel, Sr.,1884-1975,左)和社会学家李景汉一起,去北京郊外妙峰山进香。美国杜克大学图书馆西德尼·甘博照片专藏慨允使用。
一个工作坊建起来了,赤贫家庭里的妇女都被召集过来做刺绣活儿。我被分到的第一份工作,是进去带她们做操;因为她们整天都弓着身子在那儿做针线活儿,需要站起来伸伸胳膊。然而,她们主要的活动却是放声大笑!首先,她们觉得这样的动作太可笑了,其次,她们笑我的汉语说得笨嘴拙舌,我在语言学校就学了一个月的中文(译者注:1920年富平安在北京的华北协和语言学校暨The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学习中文)。所以,我们每天都要哈哈大笑半个小时。(图10)
图10:约1922年,美国公理会在北京郊外组办贫民妇女手织工作坊。这是工作人员和工作坊的女子合影。前排正中坐在一名白裙美国妇女和一名黑裙中国老年妇女中间的就是富平安。
我没有被要求去传福音,这不是派我来的公理会的工作重头。我只是在北京的国立中文大学(National Chinese University)教过一节《圣经》课,我知道那些男生是为了学英文才来的。那节课是讲阿摩司书(book of Amos),选这个主题是想告诉他们说,一座城市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在北京成家
我第一次去中国在那儿呆了五年,后来我再次去又多呆了两年。
我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是单身,但到了北京三年以后就结婚了,就是在那里我遇见了我的丈夫,在中华医学基金会(medical board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工作的富路特(译者注:L. Carrington Goodrich,路德·卡林顿·古德里奇,1894-1986,中文名也作傅路德、富路德,美国汉学家。著有《中华民族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和《明代名人录/Ming Biography》等)。“L”是指“路德/Luther”,这个名字是随的他的外公,在部队时他被叫做“路德”(译者注:1918年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富路特入伍被派往法国,协助基督教青年会暨YMCA为中国劳工旅做翻译),不过这个全称后来几乎没用过(译者注:任职哥伦比亚大学后,富路特一直被称作卡林顿/Carrington)。我也很为我名字中像“斯旺”和“古德里奇”的这些部分感到自豪,后者能追溯到英国怀河(River Wye)边古德里奇镇上的古德里奇城堡(Goodrich Castle),毁于1066年。(图11)
图11:1923年,富平安在富路特位于协和医学院的中华医学基金会办公室门前,门上有名牌(L. C. Goodrich)。
他从事的工作带有“传教”的性质,这仅限于说他要代表教会医院去向洛克菲勒做汇报,看它们是否应该得到经费,不论开办这些医院的目的是为了医疗还是为了传福音。洛克菲勒基金会对医药业的投资和改进农村的大众卫生状况,都是很感兴趣的。
我是1923年2月2日在中国北京结的婚,那一年我28岁,和我的丈夫同年。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哦,他的父母是传教士(译者注:富路特出生于中国通州。父亲昌西·古德里奇/Chauncey Goodrich,1836-1925,美国公理会教士,1865年来华传教,中文名“富善”,中文和合本《圣经》翻译主持者之一,编有《富善字典》;母亲撒拉·伯德曼·古德里奇/Sarah Boardman Goodrich,1855-1923,1879年来华传教,中文名“轲慕慈”,曾任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暨WCTU中国总干事,倡导禁鸦片和反缠足运动。富善与柯慕慈1880年在北京结婚,逝世后皆葬于通州,墓地今毁),就住在我居住的学校对街的院落里,很难“不”遇到他。而且,我必须说,他很有女人缘!(图12)
图12:1923年2月2日,富平安(右)与富路特在北京举行婚礼。
我丈夫的父母亲也都是公理会的传教士,有人会说,尽管这个会当然也有“灵性”关怀和启示,但他们对中国人的福利的关注要多过“拯救他们的灵魂”;而其他教派则热衷传教,企望把越多中国人改造成基督徒越好。在北京我遇到了我未来的婆婆撒拉·伯德曼·古德里奇,她不仅是传教士,而且是在中国行动着的力量。她是一位“妇女解放者”,在人们还不明白这个词的意义之前她就是了。有一次,为了给人力车夫筹钱新建一个歇脚处,她督请当地的执政者和她一起在那里过夜,想让他看看那个老地方有多冷有多破。执政官不肯去,但拨给了她筹建风雨亭的款项。我一直是在干实事儿的女性身边长大的,有学习的好榜样。就像哈里·爱默生·弗斯迪克启蒙了我的自由主义思想一样,我的婆婆由里到外的自由主义做派也影响了我,我的女儿安(Anne)就是这么说的。(图13)
图13:1903年富路特与父亲富善神父、母亲柯慕慈、早逝的二姐和大姐葛丽丝(右立,Grace Goodrich,1889-1969,1920年代在燕京大学教授声乐,1940年代在“美国之音”汉语广播电台工作)。
我结婚的时候,原本准备在北京能找到啥就穿啥;但我的大姨没有听见我的想法,她给我寄来了华丽的婚纱和面纱,是纽约最时髦的款式。我的姨妈想要我在那一天美美的!她还给我寄来了一顶用羽毛装饰的帽子,在结婚旅行时可以戴着拍照相用的;但我当时却是穿着工装裤,因为我们到一个陵园里去野营去了。这听起来很吓人,但是中国的陵园是不一样的,那里还有小屋子可以租住。人们听说我们去了,小孩子们都跑出来欢迎我们。太棒了!(图14)
图14:1923年富平安在北京举办婚礼时,穿着大姨从美国寄来的纽约最时髦款式的婚纱。
在和卡林顿约会以前,我从未骑过马。他常带我出去骑马,体验体验。我们去到北京的城墙外,骑马穿过开阔的原野。有一次,我跟着他疾驰;当他和他的马跃过一段土沟时,我完全没有选择只能是跟过去。他回头看见我离开马背悬在空中,事后他惊呼,看到我正正好好地落回去,他是多么惊讶。我们每天都在马背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结婚以后,我就不大做传教士的工作了,除了还去那个小作坊,帮那些女人在做针线活儿的间歇时间里,做些伸展运动。那时起,我的工作更多是自愿性质,教会不再付报酬了。
后来,我们又回到中国住了两年,那次我们回去,是因为我丈夫要做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他也在语言学校教课,那时候变成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的一部分。他拿着奖学金,不再受雇于洛克菲勒基金会了。
我在传教工作中,生发出了对中国人民的热爱以及对他们全神崇拜的痴迷,那些神都是某段时间里曾经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真人。食物太棒了,没有比中餐更好吃的了;而且中国人是那么可爱又善良。除了可怕的卫生状况,我几乎爱上了北京的一切。当我回顾我做过的各种事情时,我的女儿安提醒说我还曾得过“华北潜水冠军”呢。我丈夫当时在上海出差,他是从报纸上得知我获奖的消息的。我现在不是一名好潜水员啰,但是按照潜水规则里规定的三类,我可是“三种全会”哒!我当时不得不学第三种。一个人如果想要做什么,可能就需要在所有座右铭之外再加上这么一条——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图15)
图15:约1931年,富平安在北京参观寺庙。美国杜克大学图书馆西德尼·甘博照片专藏慨允使用。
我的小家庭
当我们还在中国时,我和我丈夫成了家,最后养了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他从事他的教书生涯,我带着五个小孩儿,比他还忙,就算孩子们还很小的时候,我也在所在地的教堂里做些信仰教育的工作,最初是义工,后来成了有薪资的职员。当然,一家人一起也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有一次去蒙大拿(Montana)旅行,为了省时间,我们准备乘上午出发的轮渡穿过密执根湖。可是没有找到过夜的地方,我看见路边有一大块空地,就决定停在那大块地的中间,在车里歇息。一夜安顺。可是早上我们却发现那块地的周边有一条壕沟,只有一条特别的小道通得进去。那么,我们是怎么在黑暗中跨过那条壕沟的呢?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它的存在。(图16)
图16:1938年,富平安夫妇和孩子们的全家福。后排是大儿子弗朗克,前排左一是小女儿安,左二是二儿子托马斯,左三是小儿子哈伯德,左四是大女儿萨莉。
我的老大是弗朗克(译者注:Frank Chauncey Goodrich,1924-1980),1924年出生在中国。他是个好男孩,不过他的幺妹指出一个例外,她记得他常常往其他孩子们的脚趾缝间扔飞镖。他很机灵,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化学的博士学位,之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做过飞行员。起先他在加州一家大型石油公司工作,但他后来不想从商了;在纽约州的一所技术学院获得了化学教授的职位,别的教授们都认为他是能得诺贝尔奖的;但是他在其他领域也一样聪颖,他还教授地质学,爱好民族舞和弹吉他。他的指导老师说如果他专注于弹吉他,他定能成为全国的第一吉他手。多年前他被杀害了(译者注:弗朗克生前供职于纽约州波茨坦市/Potsdam的克拉克森学院/Clarkson College,据1980年11月的当地报纸报道,弗朗克死于一起故意杀人案)。
汤姆(译者注:Thomas Day Goodrich,1927-2015)是我的第二个孩子。他很讨人喜欢,哥伦比亚大学教务长的太太就说:“富路特夫人,您的孩子们都好棒,可我就是喜欢汤姆。”我想他真是从未遇到过麻烦。他去威廉姆斯学院有些年,然后他被选入军队并到日本效力于麦克阿瑟(MacArthur)将军。之后,他从圣巴巴拉(Santa Barbara)的加州大学获得了学位。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获得硕士学位后,教过小学四年级。随后,可能是受到他母亲经历的影响,他去了公理会美国差会,到土耳其教了七八年的男校。然后,他在印第安纳宾夕法尼亚大学(Indian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教欧洲史和奥斯曼史。关于奥斯曼土耳其人对美国的最初认识,他写过一本有趣的书(译者注:1990年版《奥斯曼土耳其人与新世界/The Ottoman Turks and the New World》)。汤姆现在住在特拉华州(Delaware)的威尔明顿(Wilmington)。他是中世纪地图方面的专家。
萨莉(译者注:Sally Boardman Goodrich,1929- ,今名为Sally Boardman Goodrich Hurlbert)是我的第三个孩子,和她的哥哥汤姆一样,出生在纽约市妇科医院。她从小就很有乐感,唱歌很好听。她去北加州读贵格会学院,是个人缘很棒的好学生。她也从哥伦比亚大学的教师学院获得了硕士学位。结婚以后她教幼儿园和一年级。她让她的小朋友们看母鸡孵蛋,在学校里教音乐,也做私教。现在她住在康涅狄格州的埃文市。
最小的孩子是双胞胎安(译者注:Anne Perkins Goodrich,1932- ,今名为Anne Goodrich Jones)和哈伯德(译者注:Hubbard Carrington Goodrich,1932- ),1932年出生在中国,那时我们回中国去是因为我丈夫要做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哈伯德比他妹妹早七分钟出世,用我丈夫的叔叔哈伯德的名字命名的。小时候就略去不表了吧,就说长大以后,他也许真没把自己当大学生看,虽说他是拿到了本科学位了的。后来为了教外国人说英文,他还从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拿到了硕士文凭。他在哥大修读过博士课程,但是由于学生运动的影响,一直都没拿到学位。哈伯德在阿富汗做英文教师培训做了九年,二十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他游遍了那个国家。
我每年在缅因州哈南普斯维尔市(South Harpsville)的一个小渔村,与哈伯德和我的儿媳住上五个月;其他时间我和他的双胞胎妹妹、我的女儿安住在佛罗里达州的安娜·玛丽亚(Anna Maria)岛。我第一次到佛罗里达的时候,是和她一起住在迈阿密;那时我常常去养老院和大家一起锻炼身体,很开心。(图17)
我必须说,安在所有的宝宝中是最可爱的。她出生时只有五磅重,那么小巧那么漂亮,医院其他部门的护士们都跑到产科病房来看这个小宝贝。最终她从哥伦比亚大学内科与外科学院的理疗系毕业,工作到1996年退休。医院总是把需要额外护理的特殊病人派给她,有一次,医生都放弃希望了,安还是帮助病人恢复了手的活动,之后还能走路了。我想,安对病人是有魔力的,我认为那是一种治愈的魔力。她的丈夫泰利(译者注:Terry Bass Jones),也是理疗师,是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理疗系的系主任,在那之前,他在艾奥瓦(Iowa)的一所理疗学校做主任。
女儿安帮我算了算,目前我有12个孙辈和46个重孙辈,还要加上很多继孙辈和继重孙辈。(图18)
图18:约1985年夏天,富路特家族到缅因州举办例行的亲友聚会,大部分子女和他们的伴侣以及孙辈到场。前排左二是富平安,左三是富路特,左一是儿子托马斯;后排左二是女儿安,左四是儿子哈伯德,右一是女儿萨莉。
我们一生中的中国
我丈夫为洛克菲勒基金会工作,检查基金会在北京设立的医院的卫生情况,也被分配做些其他的工作。基金会结束了他在中国的工作后,付了他一年的薪水;然后我们就回到纽约落户(译者注:1925年富路特一家七口返回纽约)。我丈夫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他学习中国历史,同时也教汉语,因为他说汉语。随后,他在哥大获得了博士学位,也开始改进东方历史的课程,并在那里到达成功的巅峰,成为“丁良讲席教授”(译者注:Dean Lung,音译为丁良,也作丁龙,赴美华工,美国商人、律师和官员贺拉斯·沃尔普·卡朋蒂埃/Horace Walpole Carpentier的家仆。1901年卡朋蒂埃向母校哥伦比亚大学捐款10万美金,在哥大建立以其仆人姓名命名的“丁良汉学讲席”,丁良随后也捐出积蓄1.2万美元。以此为起点哥伦比亚大学中文系创办了起来,即现在的东亚语言与文化系。富路特1927年在中文系获得硕士学位,1934年获得博士学位。1926年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中文系任教,1947年获得“丁良讲席教授”职衔,1961年退休。)。他做了27年的系主任,直到退休。很偶然,我丈夫早年的一些学生还和我保持着联系,这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
我的女儿安记得她的父母都是社会活动家。当日本拔出刺刀时,我在美国印刷传单,呼吁民众不要把金属废料卖给日本以制造战争武器,也不要买他们的丝袜,因为这些钱会被日本用于战争(译者注:1942年前后的若干年中,富平安都在为两个美国民间组织工作,它们都旨在筹集经费、购买并捐献物资,帮助中国抵抗日本侵略:一个是活跃于1938年至1941年的“美国不参加日本侵略委员会”暨American Committee for Non-Participation on Japanese Aggression,另一个是于1941年在纽约成立的“援华联合会”暨United China Relief)。我和我丈夫1938年计划返回北京,直接就被日本侵略者勒令遣返了。(图19)
图19:1981年10月16日至11月7日,富平安和富路特与爱好中国历史文化的美国学者和友人一起,经香港,到杭州、苏州、北京、大同、西安、敦煌和兰州做了一次定制的文化考古之旅,后经广州返香港飞回纽约,总计21天。这是他们自1932年返美后首次回到阔别已久的中国,富平安夫妇在北京寻访了他们和父母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也是在这次旅行中他们发现富路特的父母和兄姊的墓地已毁。
五十年代的时候,我丈夫在印度的大学教书(译者注:1953至1954学年,富路特教授作为富布莱特学者赴印度维斯瓦·巴拉蒂大学暨Visva Bharati University讲授中国历史),我们在印度住了九个月。去印度的旅行是我一生中的高光时刻。这个国家和美国那么不一样,生活和习惯与我们都不同。我非常生动地记得那些日子。我骑着自行车穿行在村庄,看到那儿的人民是如何生活的。他退休后,我们去了一年日本(译者注:富路特教授1961年退休。1961至1962学年,他受邀赴日本东京的国际基督教大学暨International Christian University任中国历史访问教授)。除了去中国、印度和日本,我和丈夫在澳大利亚住了六个月(译者注:1960至1961学年,富路特教授借调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暨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开设中国历史系列讲座)。我们也有在俄罗斯的有趣的旅行,特别是在历史名城撒马尔罕(Samarkan)。那儿早期的建筑那么漂亮。知道它是一个真实的地方而不仅仅只是一个传说,这真让人兴奋。我见到过的俄罗斯可能和大多是人见到的一样多,或者多一点(译者注:1960年8月第25届国际东方学学者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富路特教授应邀出席,随后考察了前苏联若干加盟共和国的中国研究概况)。我还去过大多数的欧洲国家。
旅行,带我去过超过85个不同的国家,是我有过的美好生活中的华彩篇章。(图20)
图20:1987年富平安带领家族11人回访中国,这是在参观由她婆婆撒拉于1904年创立的“安士学道院”,1926年更名为“富育女学校”(Goodrich Girls School),即今天的“北京市通州区第二中学”前身。
我在中国的时候开始对中国人的信仰感兴趣,这开始了我的写作生涯。关于中国人的信仰,我写了四本书(译者注:除了《禄是遒中国迷信研究索引》暨Index to Chinese Superstition by DORÉ没有出版外,其他三本均由西文汉学界著名的机构“华裔学志”出版,分别是1964年的《东岳庙》暨The Peking Temple of the Eastern Peak、1981年的《中国地狱:北京十八地狱庙与中国人的地狱观念》暨Chinese hells: The Peking Temple of Eighteen Hells and Chinese Conceptions of Hell和1991年的《北京纸神:家庭祭拜一瞥》暨Peking paper Gods: A Look at Home Worship),包括一本关于北京东岳庙的,那是一座综合庙宇,被毁掉了,后来改建成一座博物馆(译者注:东岳庙,现在是北京民俗博物馆的所在地),用了我的书做修复的参考。我最近的一本书《北京纸神》,是关于灶神和其他家庭祭祀的神祇的,是在我95岁的时候出版的。103岁我写了我最新的文章(译者注:《妙峰山》,发表于1998年第1期的《亚洲民俗研究》学刊)。(图21)
图21:由华裔学志出版的富平安的三本著作:《中国纸神:家庭祭拜一瞥》、《东岳庙》和《中国地狱:北京十八地狱庙与中国人的地狱观念》。
我得到并保存了很多年的特殊物品中,也许首要的,是我的婚纱,现在还在。结婚五十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我还穿过它。很多东西我都保存至今,因为它们对我有意义。其中有一块中国长城的砖,是我的公公从一大块墙体上切割下来的一小块。几年前在佛罗里达州的安娜·玛丽亚小学演讲,我把它和其他东西一起带了过去,就这块砖,激起了孩子们最大的兴趣。虽然我听说长城是能从太空上唯一能看到的地球上的物件,但我觉得其实很难,因为很多城墙都在树丛里面了。
我的政治观点及对信仰的想法
1920年,没有比女性首次投票更重大的事情了。我记得没人大惊小怪。人们觉得投票是理所应当的,就像我们总是在新事物到来的时候接受它们一样。1920年美国女性首次被允许投票时,我就参投了;我那时过了21岁,能够投票。我本来要投票给阿尔·史密斯(Al Smith),但是后来听说他什么女人都乱搞,是个十足可怕的男人。从那以后,只要我人在美国,我次次都投票。
我的大伯尽管从政,但他并不试图告诉我该怎么投票。他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不要告诉别人你把票投给了谁。虽说我是美国匿名投票制度的忠实信徒,但我不介意说出我所有这些年我大部分是投票给了民主党。
关于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我觉得他婚外情的丑闻应该是他的私事。当然一切都是政治,共和党不能用选票将他阻止到办公室外,就努力用另一法子把他赶了出去。并不是每一位上了榜的民主党总统我都喜欢。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很糟糕,他做什么都做不好。我不喜欢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他太霸道了。我也不喜欢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她过去常常写专栏,写怎么养育孩子,但自己却并不呆在家。不过,后来,我开始欣赏罗斯福夫人(译者注:罗斯福夫人曾任援华联合会的名誉会长)。我认为她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人,无论男女。
我自己的宗教信仰这么多年都没有改变过。我一直是比较倾向于自由派基督教(译者注:Liberal Christianity,也译作自由主义神学,是当代基督教的现代主义运动的产物),受到哈里·爱默生·弗斯迪克博士的影响非常大,还有一位是叫做博格(译者注:Marcus Joel Borg,1942-2015,美国新约圣经学者,耶稣研究会的成员,耶稣历史研究的代表人物)的神学家,可能不太有人知道他。他们的关注点(包括我的)在于耶稣是一个人。博格和很多人一样,说开始的时候,他接受的是有关东正教的完整的教育,但是后来他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如今,我对“耶稣研究会”(译者注:即Jesus Seminar,是以圣经批判为基础的非宗教性学术研究团体,活跃于1985年到2006年间,倡导对耶稣的史实性研究)的研究和作品都很感兴趣,他们的侧重点是历史上的耶稣。
结语
我总是很忙,忙得没有时间去变老。特别是在孩子们都长大了以后,我试着通过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并为其他人做些贡献来保持生命的活力。首先,我总是忙于教会的事情。我总是在那里忙碌着,他们不能赶我走(译者注:以1960年为例,富平安65岁,出任纽约布朗克斯区新教理事会基督教育委员会的主席,在住所附近的教堂讲授圣经课程,还在一个公益性质的推介印度民间手工艺品的公平交易组织中担任主任一职)。对我而言,比我老十岁那才叫老嘛。更大程度上,我的健康长寿是不是要归功于我对于各项体育运动一贯的兴趣和参与呢?这倒并非偶然。人们总说我苗条又瘦小,不是典型的运动体格。但是我的孙女卡琳娜·黑尔斯(Kaline Hills)却说哪怕我到了85岁还能“猛击网球”呢。我喜欢打网球,但我从没觉得自己是个好球手。后来呢,倒是我的丈夫,要成网球运动员了。卡琳娜还记得她的祖父母快90岁的时候,和她一起去过卡罗拉多的牛仔牧场玩,我们一起骑马,还和年轻人一道玩激浪漂流呢。1987年,我91岁,我和孩子们一起回到中国,活力爆棚。(图22)
图22:富平安在划船。这艘小船是1995年她一百岁生日时女儿安送给她的生日礼物。
活过了完整的二十世纪,人们问我会如何推测二十一世纪的生活。我期待科学家们会发现所有令人兴奋的事物。有一天每个人都能够自己飞行,那时候天空会很拥挤,而不是挤在路上。我们能到月亮上去玩玩,在上面散散步。
曾有人问我一生中是否有什么事情是我想做而没有机会做的,我不得不说,所有我想做的,我都做过了。我不介意重过一遍我大部分的生活,好比说从我去中国,认识我丈夫,到他去世的1986年。我生活的大部分快乐源于他,他甚至在我的书籍的出版中也尽了力。我知道生活在改变,而且你除了随机应变并无他法。我喜欢我见到的很多变化,我也觉得世界正在变得更美好。(图23)
图23:富平安和富路特,1954年在美国夏威夷州的檀香山。
【译者说明】
富平安女士(1895-2005)的自传写作于2002年。2020年5月,经富平安的儿子哈伯德·卡林顿·古德里奇先生和女儿安·古德里奇·琼斯女士书面授权翻译许可,并允许经译者整理、编写并加注释后发表。译者为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民俗学研究所教授。原题为《富平安自传》,现标题(含小标题)、注释和图片说明为译者所拟,注释和图片说明主要依据的是瓦萨学院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和杜克大学图书馆所藏档案和富平安亲友的访谈资料。所附图片除特殊说明外,均经哈伯德·古德里奇先生和安·琼斯女士慨允使用,版权所有。
译者节录了自传原稿中与中国直接相关的内容,以《我一生的中国》为题,首发于2020年6月5日的《文汇报·文汇学人》。这里是经过编译的全文完整版。这篇自传表明,富平安女士是接受了典范“美式精英教育”的女知识人,但她同时也受到了中国民间信仰和中华传统文化的终生感召。她的故事,尤其是她内化于自由派基督信仰的中国民间信仰情结,是不同文明间交往与交流的珍贵叙事,不仅以个人生活史的方式再现了二十世纪中美两国的社会变迁,证明了中美民间文化流转的命脉深埋;而且以此为背景,互为他者地见证了不同信仰的共通理性和终极追求的普遍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