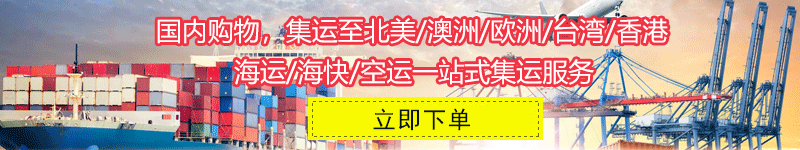埃里希▪蒂斯(Erich Thies),曾任德国海德堡师范学院院长,柏林教育科研部国务秘书,联邦德国文教部长联席会议秘书长等职,现为国家汉办高级顾问、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曾获“德国一等十字勋章”等荣誉。
“在欧洲民粹主义崛起与盛行,政治力量格局悄然发生变化以及欧盟一体化理念日渐模糊的大背景下,本文作者通过挖掘大量有关‘犹太人流亡上海’的珍贵档案史料,试图在‘二战期间犹太人为逃离纳粹魔掌流亡上海’与‘当下中东战乱国受迫害难民由于种族和宗教原因流亡欧洲’之间建立关联,就当前德国乃至欧洲各党团及社会民众在难民接受问题上所存在的分歧,提出‘流亡与避难’这一组合表达;行文穿梭在‘历史和当下’、‘中国和德国’两个时空层面,意在希望这种交替和关联所形成的全新认知和情感张力,能促使德国无论在国家,还是社会层面,找到一条介于道德义务和政治实用主义之间的正确道路,继而引导民众逐步接受德国可以成为避难之地。”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姜锋教授如是说。
埃里希▪蒂斯教授流亡与避难
“避难”(Zuflucht)一词在很大程度上已退出德国人如今的语用习惯,也许在与“教堂避难”相关的方面或者在赞美诗中还会用作对上帝的祈求。“寻求避难”的意思是寻找一处能够提供住处的安全地方,而非房屋或者甚至家乡。“避难”与“寻求避难”迄今为止对大多数德国人没有现实意义,德国人已无法在情感上切身体会其完整的意义。德意志民族的语言组合“流亡与驱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性产物,形式化且象征性地表达了遭受的不公,并已纳入政治语汇。“我们失去了一切”——这是当时的表述。财富、家园、朋友和亲人统统不在,只留下历史等待人们去追忆。
“热情好客”并不一定属于德意志人的美德准则,因此,即便是为外国人提供避难之地和“给予庇护”对德国人来说都是一种新的,还未形成习惯的经历,尚需要进一步的解释。
人们寻求避难,并且在某处给予庇护的地方找到避难所,常常是最后的、唯一的避难之处。但“庇护”(Asyl)这一概念源自希腊语,意味着无争夺、安全。庇护权有两种类型,即国家庇护权与教会庇护权。迄今教堂仍为遭受迫害的人提供特殊庇护;曾经触摸特定的宗教物品就意味着庇护,并且形成了庇护权。违反这一权利被认为是一种亵渎,必须进行赎罪。1951年日内瓦国际公约对国家庇护权进行了规定,德国已将该庇护权编入宪法。如果寻求避难者身处申请避难国的大使馆的治外法权之地,也同样可以申请特殊庇护。
“流亡与避难”和“生与死”、“疾病与健康”以及“战争与和平”一样,都是关乎个体命运的大主题。在受害者眼中,这就是命运、运气、厄运。“生与死”、“疾病与健康”会涉及每个人,而战乱、驱逐和种族灭绝则是社会结构与国家行为的后果,取决于作为或者不作为——无论是政治原因、种族原因,抑或是宗教原因。一个地区信奉某宗教的人都处于阴影笼罩之下,这种阴影突然决定了他们共同的生活处境,但没有人会为他们未来的生活创造真实而有生机的共性之处。只有破坏;摧毁了过去、现在与未来。迄今为止的一切都已失去,导致的后果是恐惧(Entsetzen)——安顿(Setzen)与拥有(Besitz)的反义词,属于我的一切一下子都被夺走,令人措手不及。
“流亡与避难”的存在意义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变化。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犹太人因纳粹的种族灭绝流亡中国,如今中东难民逃离战乱,对直接受害者而言是相同的:逃往另一个安全之地,以保全生命。
近年来的流亡与避难
德国警察和小难民交谈。我们的时代又是大主题的时代。“流亡”与“避难”这两个主题操控着公众的注意力以及国家和政治的行为。大主题迫使我们不得不摆明立场与观点,这就造成全新的政治党派力量格局以及政治权力的明显转移,迄今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社会共识被打破,甚至使之消失,仿佛从未达成过共识。人们对迄今为止的事情产生怀疑,又或者认为:那也只是随着时间自然发生的,似乎不需要特殊的反思和努力。
流亡与避难对大多数的德国人而言是陌生的,是历史上久远的话题,或者认为那只是世界偏远之地才会发生的情况。然而实际上,多年来一直都有难民申请德国庇护。只不过短期内寻求庇护者的数量激增导致“流亡与避难”这一主题发生新的质变。法定移民、避难申请流程的合理处理、大批难民的安置和融入、对城市与乡镇带来的影响、对经济与教育体系的影响,这些问题毫无预兆地涌现出来,令人不知所措。此外,难民问题还与人们对潜在恐怖袭击的恐惧联系起来。前几年公众关注的中心话题“银行危机”、“希腊问题”、“能源政策转变”和“环保问题”都被湮没了。而欧盟及其扩张计划则变得不再理所当然。“流亡与避难”导致了欧洲范围内过往无法想象的党团分化,许多人开始质疑引领欧洲一体化的理念。“英国脱欧”及其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以及经典联盟“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马耳他”的解体,都是难民话题引发的尖锐而令人震惊的后果。这些后果使一种典型的民主原则的合理性以及全民公投这种直接民主方式的界限有了新的意义。
这个大主题导致社会被分裂,公众大讨论使得政府决策者突然都为各自国家的理念和方案辩护,欧洲一体化理念日渐模糊,甚至要消散。这一大主题甚至迫使每个人都去思索他所愿意持有的姿态、社会的道路应通往何方、欧盟各国的政治形势又将会怎样。仿佛欧洲联合的理念以及与其相联的政治与道德准则和历史根源全被遗忘,并且在近几年里逐渐消弭。看上去似乎只剩下赤裸裸的经济与军事利益能将欧洲国家联系起来。
德国社会也在经历深度的分裂。关键词“欢迎文化”及其象征姿态是一部分德国人民的特征,是大部分的,正如我所认为与希望的(民调显示,大部分人支持“欢迎文化”,即使人数有所变动)。当然也出现了小市民的民粹主义,极端势力抬头,并与某些政治党派相关联。也有人表现出恐惧与憎恨,有人表现了淳朴与善良。无论是一部分人拒绝难民的极端程度,还是另一部分人明确而积极的热忱相助以及所表现出的社会担当,都超过了所有预期。德国人看着自己的国家要成为“避难之地”,而且以这样一个未曾预见的规模成为战争难民和种族与宗教的受害者的目的地,这对德国人来说,是一种新的、令人迷茫的经历,且似乎仍未找到真正强有力的表达方式。
德国民众欢迎难民。媒体每天将各种无法不令人动容的照片植入公共意识,这些照片构成整个主题的标识。随之而来的溺亡难民数量也因为媒体持续报道的大数目而变得模糊不清;数目之大,似乎已超出我们的理解力。悲剧事件由于几乎模式化的重复而变得无所谓。只有那伏尸海滩的小男孩画面始终在眼前,而其他许许多多的事件却变得抽象而遥远。
“流亡与避难”的出现弱化了其他人们喜闻乐见主题的意义。那些照片已经让我们无法再执着于阅读饮食文化专栏或者其他说明我们相对而言还极为富足的文章。“流亡与避难”的画面与我们日常习惯的生活质量格格不入。这是一种新的经历。迄今为止自然而然的事物遭到破坏,却可能隐藏着新的契机,因为已经损坏的不能再重建或恢复。从破碎之物中,人们也许能够产生一种全新的自我认知。
犹太人流亡上海
1938年11月的“水晶之夜”后,德国对犹太人实施大屠杀,纳粹开始了有计划的掠夺:存款、房屋和其他的财产都被洗劫一空。柏林的美国领事馆曾经在一天之内下发了两千八百份签证申请,但西方主要国家都不准备向犹太人开放,甚至没有对纳粹迫害犹太人进行谴责。表面上,人们说那是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造成的,实际上却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排犹主义。许多犹太流亡者心仪的目的地是美国,但美国并未准备提高接受难民的比例,还要求难民签署“宣誓书”——这是一种经济担保,难民必须保证在当时艰难的经济条件下不对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造成负担。圣路易斯号客轮事件便是最好的说明。美国反对接纳难民的声音也越来越强:国会与国务院在三十年代借助迟疑策略和官僚策略,使得法律规定的一定数量的德国移民都无法入境;各工会团体强调高失业率与经济危机。与此同时,美国利用其政治影响力使得其他国家也无法接纳多余的难民,如古巴、当时还独立的阿拉斯加、瑞典(战后,美国对想要移民美国的上海犹太难民也持类似的态度)。
与此相反的是,难民可以没有签证去中国上海。上海作为避难之地,不是家园,而是“等候大厅”、“上海走廊”、“旅馆”或者“流放之地”,尽管当时也有过限制难民流入的考量。《上海犹太纪事报》上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幸运的是,人道主义关怀的思考占了上风,上海现在要为成千上万不幸的人提供庇护——或者说是幸运之人,因为他们能够在希特勒大开杀戒之前离开欧洲。”
犹太人的具体避难处是“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直到1943年2月,犹太难民被日本占领军强制迁往到虹口的难民隔离区。当时上海已有相当多的犹太人,主要是俄罗斯犹太人,在当地做生意,过着富足的生活。但这只是例外。德国驻沪领事馆1940年1月11日发给外交部的报告,以清晰的纳粹语气写道:“素来就有犹太人生活在上海。作为向中国后方扩展的入口,这座百万人口的城市有着独特的经济意义,其租界特殊的政治结构使得这座城市始终是大家进入中国的始发地。这里盛行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精神、法国人的心胸宽广,使得犹太人能够融入当地经济生活,这也最符合他们的特点,同时也赋予他们获得财富与影响力的机会。战争爆发之前,上海的犹太人总数约六七千,其中约一千人生活在虹口区,两千人生活在公共租界,剩下的居住在法租界。一些来自巴格达和孟买的犹太人家族已经几代人生活在这里,他们主要靠鸦片生意积累了财富。”
犹太难民在上海的居住证。犹太人在上海的岁月受到复杂政治结构与截然不同的利益形势的影响。当时上海本身处于被侵略的不安全状态。1936年,德意志第三帝国与日本共同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并结盟,使得流亡到上海的犹太人也畏惧日本占领军及其在南京的傀儡政权。珍珠港事件之后租界被日本占领,在此之后,主要是上海属于中国的部分为犹太人提供入境的机会。
此外,被德国占领的各地区都建立起纳粹分支机构与盖世太保组织。1942年万湖会议决定对犹太民族采取灭绝行动,之后,恐惧蔓延开来,上海的犹太人也担心无法逃脱纳粹的迫害。盖世太保驻日本首席代表、声名狼藉的“华沙屠夫”约瑟夫·梅辛格现身上海,与日本占领当局对话,提出屠杀犹太人的“上海最后解决方案”,使得恐惧愈演愈烈。梅辛格试图让日本人建立犹太人集中营。他甚至残暴地建议,用船只把犹太人送到海上,然后将其沉没,或者运送到岛上去,让他们在那里饿死,帝国外交部由于时机等原因制止了该建议。
德国柏林外交部档案馆中陈列着当时北京德国大使馆以及驻沪领事馆的卷宗。中国人杨先生(YANG Sen Po)与来自莱比锡的犹太人艾玛·爱思特·萨拉·杨(Emma Esther Sara YANG)结婚故事体现了中国人对犹太人的态度。1943年11月27 / 28日,这位犹太女士在格拉市附近被盖世太保逮捕并送进了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她被托特组织强制要求劳动。她的丈夫杨先生寄来一封信,质问盖世太保缘由,引起了帝国外交部与帝国中央安全局就如何处理这位嫁给中国人的犹太女人这一问题进行政策辩论。这场政策辩论围绕相对抽象但绝对德国化的问题,然而却是受害者生死攸关的问题,即应当怎样处置与中国人通婚的犹太妇女。帝国外交部请求将这类犹太人按照中国国籍来处置。1944年12月13日,外交部的所谓犹太顾问塔登(Thadden)写道:“面对东亚在种族问题上的敏感,期待采取针对远东德国人的相应措施,作为我们对这一单个事件进行处理的结果。”档案中并没有提及艾玛·爱思特·萨拉·杨的结局。
犹太难民与中国的关系、与中国人民的关系,以及与日本占领军的关系,作为特殊政治利益都在北京德国大使馆以及驻沪领事馆的报告中得到着重的记录。因为日本作为轴心国之一与德意志帝国结成联盟,与中国挑起战争,而中国本身内政就处于一种蒋介石与毛泽东相对立的分裂状态。一篇题为“犹太人在上海”的报道在1940年7月30日寄到了帝国外交部。上海方面并没有同意贯彻万湖会议的秘密决议,佐证这一点的还有以下一些例证。
外交部档案馆的一份标题为“犹太人在中国”的文件述及了日本占领军枪杀莫瑞斯·柯恩(Moritz Cohen)的事件。柯恩曾是蒋介石的财政顾问,蒋介石“曾经拥有众多犹太顾问,并且忠实听从他们的建议”,“他们使得蒋介石在与日本人无望的斗争中变得强硬”。1943年2月20日的一篇报道中叙述了日本强迫大约一万六千名犹太人迁往虹口的决定。当时犹太人已经成功地渗透到当地的经济生活中,日本占领军此举的目的是逼迫犹太人将他们的店铺转卖给日本人和中国人,这是日本占领军针对犹太人采取的第一步政策措施。
另一份呈给外交部的关于“犹太人在上海”的报道写道:“他们自我吹嘘,世界对他们的良心觉醒了,作为‘无辜的受迫害者’,他们要求得到所有人的同情……他们对中国人表达诸如此类的话语:‘我爱中国,我很高兴能来中国。’或者学习当地语言,恭维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例如犹太合唱团……将中国古典音乐搬上舞台……他们想方设法与日本人和睦相处……虹口区的日本人与犹太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还有一份报道写道:“为使犹太工程师、化学家等等通过他们种族亲人的协调在中国安顿下来,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年底出版的包含六千个名字的移民地址簿将会有助于加强联系,创建商业合作。”
1940年1月11日的一份报告中不无惋惜地总结道:“过去几年的迅猛的犹太移民,并未在其他国家公开激发接纳国的反犹情绪,这不符合期望与经验……因为移民来的犹太人还未形成影响力,因此他们的威胁性还未被认识到。他们作为可怜的受难者还被施以同情,人们还只看到了他们移入所带来的经济上的好处。上海的市场获得了新的顾客,人们确定,犹太人的店里,商品令人满意,新的裁缝店与美容院开张了,移民者适应了远东的生活。”
流亡的犹太人与日本当局的关系是脆弱的,受到持续调整与担忧的影响,也因为日本占领军1943年发布通告,要求上海的犹太人迁入“虹口无国籍难民隔离区”。之后,犹太人和日本占领君当局之间保持着一种小心翼翼的关系。这也成了当年德文报刊中许多文章的主基调。此外还有一些文章报道了反对第三帝国和侵略者日本的犹太难民被关押的消息。外交部的报道中还出现了反对纳粹的“第五纵队”。上海有一千名斗争者,他们对在国外的斗争只需要少量的补充培训……
艾恩斯特·沃尔曼(Ernst Woermann)是帝国驻日本操纵的南京傀儡政府的大使,是外交部艾恩斯特·封·魏茨泽克的后代,曾任司长和政治处处长;一位高级官员、党卫队分队长,他在1938年11月大屠杀之后由戈林领导的有关迫害犹太人的会议上,首先提出外交部的要求。艾恩斯特·沃尔曼在1946年还在上海市政府卷宗中出现过一次,在战后,德意志帝国与日本帝国的垮台后,他被送到了上海的拘留所。
1937年间,中国生活着四千五百名德国人,其中约两千人居住在上海。彼时的上海拥有四百万人口,其中包括六万五千名外国人。当中日战争的战火在1937年烧到上海,“第二次上海会战”(即淞沪会战)打响时,许许多多所谓的“德意志帝国人”离开了上海。
这正是短短几年后两万犹太人、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以及其他政治难民试图逃离欧洲的德意志政治风暴、来上海从头开始的大背景。而上海,早已卷入战火多年,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当时的上海总领事馆向德国外交部报告:“新来的约一万八千名犹太人中,约一万一千人居住在虹口区,约六千人居住在公共租界,其余则居住在法租界。”犹太人聚居地人口约两万五千,与四万日本人、两万俄国人、一万英国人、四千美国人、三千法国人和两千德国人毗邻而居。德国犹太人则作为无国籍者分开统计。
上海,犹太女孩和她的中国朋友。那时的中国老百姓很穷,虹口区遭到轰炸和战争的摧毁,并受到日本的军事管辖。流亡上海的犹太人撰写的自传式回忆录中,并没有、也无法展现出统一的中国百姓的形象。但似乎可以确定的是,犹太人认为自己受到了中国人热情好客的招待,面对上海人多舛的命运,他们无法将这种友好视为理所当然。一个地方能否让人生存下去,是唯一的标准。犹太难民、剧院经理兼作家汉斯·海因茨·兴策曼(Hans Heinz Hinzelmann)就这样写道:“长久以来,中国人早对毁灭习以为常。在虹口,人们立即重建港口和住宅区,重建市井生活的安宁和秩序。1939至1940年间发生了一些不寻常的事情:流落到中国的数以千计的欧洲难民中,绝大多数都住到了虹口的中国普通市民或工人家庭中。很明显,难民们特别理解中国百姓的处境,而他们的白人同胞则在租界里、在俱乐部中、在奢华的摩天大楼中趾高气扬,将来自欧洲的白人难民视为贱民。”(摘自兴策曼《哦,中国:古老道路上的国度》)此外,帝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指出,许多犹太人致力于“修缮那些在中日军事行动中轻微损坏的房屋,并一间一间地租赁给其他移民”。
自传中描绘的形象很多元,从中国家庭热情好客的帮助到漠不关心,再到腐朽且肆无忌惮的剥削等明显的困境。如果没有犹太人和私人的救助组织,大多数犹太难民或许无法活下来。为数不多的一些难民,曾经受过工程师、化学家、医生、药剂师或者护士的职业培训,挣到了一些钱。其他人只能靠变卖最后一些家当或靠做生意谋生,其报酬通常远远低于中国工人的工资。也有其他描述里称中国工人的处境比难民更加糟糕。
犹太难民曾在虹口区开设了小型工厂或企业,有餐馆和咖啡厅,有古典音乐会、电影院、给犹太小孩念书的学校等。虹口区建立了一种独特的市民文化生活。最明显的莫过于德语报纸了,《黄报》(Gelbe Post)则必然是其中最上档次的一份。
《黄报》——来自上海的德语杂志
在1939年5月1日到11月1日间,《黄报》最初是以七卷一百六十页的形式出版的,之后才成为报纸。主编是奥地利犹太人阿道夫·约瑟夫·施托菲尔(Adolf Josef Storfer),生于罗马尼亚的博托沙尼,卒于墨尔本,是一位心理分析学出身的出版人兼记者。定名为《黄报:东亚半月杂志》是因为黑色铅字印在黄色纸张上更清楚可读,它是流亡上海时期出版的多份德语或德英双语报纸之一。同类报纸还有《上海犹太纪事报》(Shanghai Jewish Chronicle)和《德文新报》(Ostasiatische Lloyd),后者乃纳粹宣传报纸,很滑稽的是,它一度由两位犹太难民受日本人之命编审出版,因为他们的德语说得十分之好。此外,《德文新报》几乎只字未提德语区犹太人在上海的生存状态。
其他报纸还有很多,这些在上海出版的报纸均以德语或德英双语出版——各类报纸琳琅满目,数量令人惊叹且难以估量,刊名时常更换,供难民阅读。
《黄报》是人们在虹口危险的混乱环境中的一种尝试,尝试营造回忆的德奥市民生活常态的愿景,希望以此回望故乡、联系彼此。
《黄报》的报头。人们在无数文章中探讨了迁居中国西南省份云南的问题。当时云南地区有德国和荷兰合起来那么大,没有被日本占领,而是受重庆中央政府的管辖,与其他两个省份同为抗日的中心。因而中国政府一度考虑将海南岛提供给中欧移民,作为其定居地和经济活动范围。但这一提议后由于日军占领海南岛而不了了之。通过这一过程可以发现,中国政府将外国人迁入视为完全积极的经济因素。《黄报》强调,云南省或凭借其巨大的矿产资源和日渐增长的国内外纽带的意义,前途不可限量。然而,幻想改善在上海的生活处境而制定的计划还是落空了。难民不仅担心无法应对当地中国人的竞争,且大多数难民并没有将中国或上海视为久居之地——而是过境、候车厅和上海走廊。
这些德语报纸总是刊登无数的广告,这些广告透露出报纸主要关心人们的日常生计。《黄报》的另一个基本内容体现在向难民讲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中国的历史文化成就的文章中,尤其提到了被尊为革命家和现代中国创始人的孙中山遗嘱。这些文章均对中华文化表达出极高的尊重——即使身处支离破碎的上海。
《黄报》的意图在于:“通过告知一切值得知道的东西,使移民移情上海变得轻松些。因此,除了报道租界的当地犹太人事务外,也会报道中国人的情况,并以中英文两种语言进行报道。除此之外,非常明显的是,《黄报》在努力抵制移民日渐增长的绝望情绪和自卑感。”
不仅仅是《黄报》,《上海犹太纪事报》更类似于日报。十分引人注目的一点是,《上海犹太纪事报》试着不要把和日本占领者的关系搞坏。1941年9月14日的《上海犹太纪事报》刊载了有关德军在列宁格勒战役中大败、美国援助俄罗斯以及战争转折点值得期待的文章,刊登了多萝西·汤普森(Dorothy Thompson)的文章《四位创造历史的人物:丘吉尔、希特勒、斯大林、罗斯福》。多萝西·汤普森是著名女记者,嫁给了诺贝尔奖获得者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自1924年起生活在柏林,并在那里遇到了希特勒,1934年被希特勒驱逐出境。此后,她在纽约的《国际先驱论坛报》开设专栏,公开地谴责希特勒,批判其种族理论,并普遍地批判法西斯主义。那篇刊登在《上海犹太纪事报》上的文章正是基于她与丘吉尔、希特勒和罗斯福的私交,主要涉及这几位大人物的心理学对比。她认为,丘吉尔是自由的贵族,因为他天赋异禀,无拘无束,不囿于阶级。斯大林是四位政治家中最富有人情味的,却自带一种西方人无法理解的亚洲式专制,罗斯福则是民主、自由和人性的希望的承载者,是“魔法岛”上的“魔术师”。有关希特勒的值得注意的部分将在下文完整复述。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可以从中看出,即使是这位批判的女记者也无法摆脱希特勒的影响:
希特勒身上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别人产生的影响。这样一种影响的来源实在是难以探究。
这种影响是催眠式的,或许更好地说:是魔鬼式的。他具有拿走人们的,尤其是人民大众的思考的力量。比如说,绝大多数德国妇女都认为他很俊美。
我曾经在他那儿待过半小时,在这半小时里,我十分仔细地观察他,意图将他永远地记住。
他身高五英尺十英寸,但看起来更矮一些。
他脸色苍白,皮肤很薄。额头较窄但靠后。头发柔软,发色呈深棕色。嘴几乎看不到嘴唇,牙齿稍稍内倾。他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眼睛。令人难忘。不是像他的崇拜者所描述的天蓝色,而是蓝灰色。我在希特勒那儿度过的整整半个小时中,就坐在他对面一张狭窄的桌子旁,却一次也没法和他的双目对视。它们聚焦在远处的一点上。尝试与一个不看着你的人攀谈,是极其混乱的。而且这双眼睛还有个明显的特点:尽管它们不看着你,却逼得你不得不看着它们。
一旦他被激怒,他就像着了魔似的开始说话。他说起来并不像是对着访客在说话,而像对着一个自负的听众——或者对着自己言语。他被自己感动了。他的整张脸产生了变化:脸上涨满了颜色。他在正常状态下那种标志性的羞涩和近乎谄媚的态度,产生了变化。他不是因为野心而着魔;他只是着了魔而已。
……
失望、奇异、极其不幸的形象,他自己似乎就是人民大众的一个失望且奇异的灰暗精神在现实中的代表。他营造出超重的、不祥的、累心的、魔鬼的氛围。人们对他感到敬畏,对民众感到敬畏,而他用激情统治着民众。
……
我不认为希特勒想要创造和平。原因与逻辑无关,就像那些由他挑起的战争也不太有逻辑可循一样。他就是个疯子,他的一切权力来自于他的能力——搅动昏暗的深渊,释放仇恨与失望。
希特勒身上,理智无从谈起。我肯定,他觉得自己一旦变得理智,就会失去自己的“天才”。
……
但希特勒并不介意有人恨自己,而是喜欢别人敬畏自己。那些他所面对的情绪波动,似乎只是增强了他催眠式的权力。毫无疑问,他总体上是由敌人塑造的,敌人将他变成了疯子,让他更加强大。
1945年末,难民移民意向的列表出炉。其中五千人想移民至美国,但杜鲁门坚持原有的移民准入门槛,签证的签发工作拖拉,导致爆发运动,进而导致更大规模的签证拖延。由共和党人领导的国会受反共分子和反犹分子影响,进一步阻拦了犹太人的移入。1947年起,犹太人渐渐开始从虹口区被送到美国、巴勒斯坦和德国(犹太难民和反日难民获得了国民党政府的特别居留权,甚至获得了工作许可和携带财产的权利)。“遣返”正是对此的描述。“返回”这个词并不恰当,因为遣返不总是自愿的,目的地是新的,或者是一个满目疮痍的德国。他们当初离开的德国已经不复存在,它里里外外都千疮百孔。
《上海犹太纪事报》。人们对流亡的极度恐惧以及寻求避难的迫在眉睫,以一种可怕且无法评述的方式在《上海犹太纪事报》的一篇文章《特雷布林卡》(Treblinka,位于波兰的灭绝营)中得到证实,这篇文章刊登于1945年6月29日,即第三帝国灭亡后的几周:
我们是在9月初抵达特雷布林卡的,即起义日后的第十三个月。这座死亡工厂工作了十三个月,德国人忙活了十三个月来清理工作留下的痕迹。
死寂。路旁的杉树顶端也丝毫没有动弹。几百万双眼睛看着这杉树,看着这条路,目光来自于缓缓驶向月台的专列。死寂中,飒飒作响的是黑色道路上的人的骨灰,谨慎的德国人在路两边围满了白色钙化的石头。营地上中的花儿在风中摇摆。人们觉得自己听到了来自土地深处的丧钟。脚下,特雷布林卡的土地有些塌陷,这一小块土地,几乎是一片沙漠,其中埋葬的生命要多于地球上所有的海洋。
土地将碎成小块的骨头、牙齿、物品和纸张扔出地面,它不愿为自己保守秘密。这些东西位于土地的新伤口上,位于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上。看,那儿有撕了一半的衬衫、裤子、鞋子,发了霉的雪茄、怀表的零件、生锈的刀具、毛巾等等。那儿有盘子、杯子、孩子的玩具等许多其他东西。那儿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故意将东西从地里面抽出来,有撕掉一半的外国护照,保加利亚语的记事本、在华沙和维也纳拍摄的儿童照,写着笨拙的儿童字体的便笺,一本小诗集,写在发黄制片上的祷告,一张来自德国的定量供应的纸片……在这一切之上,始终笼罩着浓重的火烧过的烟雾,久久不愿散去。地面上到处爬满了成千上万的苍蝇。我们继续在特雷布林卡肥沃的土地上前行。我们突然停住脚步。金色鬈发,稀疏的浅色女童头发,躺在地面上,已经被搅烂了。还有其他头发,深深浅浅的颜色。这或许极有可能是一大包人的头发,应该是寄到德国来的。然而这一切却是真的。最后一丝大胆的希望破碎了,真希望这只是一场梦。似乎看到了这一切,人心由于伤心和疼痛都留下来了……
德国的责任与担当
默克尔与难民合影。我想在德国对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责任、犹太人大屠杀和对因种族和宗教原因遭迫害的战争难民之命运的责任之间建立关联。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犹太人逃亡到上海是荒谬的,但上海几乎是唯一的避难地,那儿诞生的报纸应当作为背景,让这样一种无法撤销的道德、政治和国家责任具有当下现实意义。德国的当代政治讨论表明,在尊重事实和实践意义的界线上接纳难民是必要的。首先应当承认的是政治责任和由此产生的道德义务,接下来才能探讨道路和条件,确定接纳能力的边界。除此之外,已提到的痛苦的特雷布林卡语句是我们的表述,无法撤销。但公众讨论的特点则是一种无法容忍的历史遗忘,触及到我们个人人性和普遍政治的自我理解的基础。
几位中国知识分子曾在私人谈话中明确表示,他们认为联邦总理默克尔和无数其他德国人对待难民问题的态度,意味着为一个新德国盖上印章:两次世界大战和犹太人大屠杀后,它涉及一种对联邦德国具有重要意义新的政治品质。它是除二战后几十年来德国的多项政治功绩、经济成功和科技成果外,这个国家值得骄傲的又一原因。那些至少战后一代觉得不容易的东西,却很可能成为新的自我认识的完整组成部分。自豪和屈辱是并存的。
埃里希▪蒂斯教授。这些年来,“流亡和避难”这一大议题也是大的象征性姿态的时代,正因为这个议题大到可以改变德国的自我认识并为其打上新的烙印;且其程度不会影响两德统一。默克尔总理用两句核心的、政治的且与她个人紧密相连的话——“我必须坦白地讲,如果我们从现在开始还需要为在危难中展现友善的脸而道歉,那么这就不是我的国家”和“我们能做到”来表明立场,决定了难民政策中的联邦德国的道路和她自己的道路。这个国家现在的任务是,完成摆在面前的行政管理任务:将具有避难资格的难民与那些须重新遣返回国的难民区分开来。同时,国家须展现,自己能够应对由无法控制的难民入境而引起的恐怖主义危险。
人们看到:一切都没有尘埃落定。政治局势陷入动荡,没有人可以真正估量,哪些新的权力关系会产生,又将去向何处。局势动荡本质上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我们的现实也在发生变化,如果人们愿意妥善应对国家政治、经济、技术环境的变化,那么它有利于人们重新掌握本国境况。社会如果没有能力对变化的现实做出合理的反应,那么可以说社会已经开始颓败。
但是,这同样是一个尝试粗暴地抓紧当下的时代,受到不理智的、受利益驱使的民粹主义的支持,这一民粹主义甚至能够将成熟、模范的民主牵引至歧途。抓紧当下与彻底颠覆现有的东西一样粗暴。人民流露出恐惧(是被煽动的),害怕因为难民而失去所习惯的东西。对纳粹赞赏的源头来自高失业率,而复仇主义的思想则与一战的凡尔赛条约有关。这一切现在都不存在了。但似乎有一种非理性的担忧蔓延开来,外来的东西可能会搅乱习惯的生活,新的东西可能会替代熟悉的旧事物。没错,人们或许会失去可靠的财富,失去身份认同。面对这些变化,须有明确的、接纳想留在德国的难民的法律条件,须有明确的、具有强迫手段的要求,比如遵守法规、学习德语、让自己能胜任工作岗位。人们尚能期待,社会、政治和国家有能力走上道德义务和政治实用主义之间的正确道路,显示自己有能力应对新的任务,即成为避难之地。
(本文载2016年9月18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原标题为《流亡与避难——二战中的犹太人与当今的难民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