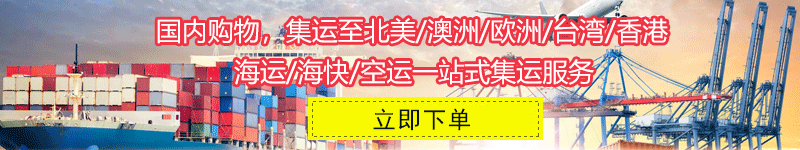这两篇文章与小坡的生日相关,转载来做参考。
老舍自传:新加坡
第四节 新加坡
一、巴黎与三等舱
离开伦敦,我到大陆上玩了三个月,多半的时间是在巴黎。
钱在我手里,也不怎么,不会生根。我并不胡花,可是钱老出去的很快。据相面的说,我的指缝太宽,不易存财;到如今我还没法打倒这个讲章。在德法意等国跑了一圈,心里很舒服了,因为钱已花光。钱花光就不再计划什么事儿,所以心里舒服。幸而巴黎的朋友还拿着我几个钱,要不然哪,就离不了法国。这几个钱仅够买三等票到新加坡的。那也无法,到新加坡再讲吧。反正新加坡比马赛离家近些,就是这个主意。
上了船,袋里还剩了十几个佛郎,合华币大洋一元有余;多少不提,到底是现款。船上遇见了几位留法回家的“国留”——复杂着一点说,就是留法的中国学生。大家一见如故,不大会儿的工夫,大家都彼此明白了经济状况:最阔气的是位姓李的,有二十七个佛郎,比我阔着块把来钱。大家把钱凑在一处,很可以买瓶香槟酒,或两支不错的吕宋烟。我们既不想喝香槟或吸吕宋,连头发都决定不去剪剪,那么,我们到底不是赤手空拳,干吗不快活呢?大家很高兴,说得也投缘。有人提议:到上海可以组织个银行。他是学财政的。我没表示什么,因为我的船票只到新加坡;上海的事先不必操心。
船上还有两位印度学生,两位美国华侨少年,也都挺和气。两位印度学生穿得满讲究,也关心中国的事。在开船的第三天早晨,他俩打起来:一个弄了个黑眼圈,一个脸上挨了一鞋底。打架的原因,他俩分头向我们诉冤,是为一双袜子,也不知谁卖给谁,穿了(或者没穿)一天又不要了,于是打起架来。黑眼圈的除用湿手绢捂着眼,一天到晚嘟囔着:“在国里,我吐痰都不屑于吐在他身上!他脏了我的鞋底!”吃了鞋底的那位就对我们讲:“上了岸再说,揍他,勒死,用小刀子捅!”他俩不再和我们讨论中国的问题,我们也不问甘地怎样了。
那两位华侨少年中的一位是出来游历:由美国到欧洲大陆,而后到上海,再回家。他在柏林住了一天,在巴黎住了一天,他告诉我,都是停在旅馆里,没有出门。他怕引诱。柏林巴黎都是坏地方,没意思,他说。到了马赛,他丢了一只皮箱。那一位少年是干什么的,我不知道。他一天到晚想家。想家之外,便看法国姑娘,尔后告诉那位出来游历的:“她们都钓我呢!”
所谓“她们”,是七八个到安南或上海的法国舞女,最年轻的不过才三十多岁。三等舱的食堂永远被她们占据着。她们吸烟,吃饭,抡大腿,练习唱,都在这儿。领导的是个五十多岁的小干老头儿。脸像个干橘子。她们没事的时候也还光着大腿,有俩小军官时常和她们弄牌玩。可是那位少年老说她们关心着他。
三等舱里不能算不热闹,舞女们一唱就唱两个多钟头。那个小干老头似乎没有夸奖她们的时候,差不多老对她们喊叫。可是她们也不在乎。她们唱或抡腿,我们就瞎扯,扯腻了便到甲板上过过风。我们的茶房是中国人,永远蹲在暗处,不留神便踩了他的脚。他卖一种黑玩艺,五个佛郎一小包,舞女们也有买的。
廿多天就这样过去:听唱,看大腿,瞎扯,吃饭。舱中老是这些人,外边老是那些水。没有一件新鲜事,大家的脸上眼看着往起长肉,好像一船受填时期的鸭子。坐船是件苦事,明知光阴怪可惜,可是没法不白白扔弃。书读不下去,海是看腻了,话也慢慢的少起来。我的心里还想着:到新加坡怎办呢?
二、国文教员
就在那么心里悬虚的一天,到了新加坡。再想在船上吃,是不可能了,只好下去。雇上洋车,不,不应当说雇上,是坐上;此处的洋车夫是多数不识路的,即使识路,也听不懂我的话。坐上,用手一指,车夫便跑下去。我是想上商务印书馆。不记得街名,可是记得它是在条热闹街上;上欧洲去的时候曾经在此处玩过一天。洋车一直路下去,我心里说:商务印书馆要是在这条街上等着我,便是开门见喜;它若不在这条街上,我便玩完。事情真凑巧,商务馆果然等着我呢。说不定还许是临时搬过来的。
这就好办了。进门就找经理。道过姓字名谁,马上问有什么工作没有。经理是包先生,人很客气,可是说事情不大易找。他叫我去看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黄曼士先生——在地面上很熟,而且好交朋友。我去见黄先生,自然是先在商务馆吃了顿饭。黄先生也一时想不到事情,可是和我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在新加坡,后来,常到他家去吃饭,也常一同出去玩。他是个很可爱的人。他家给他寄茶,总是龙井与香片两样,他不喜喝香片,便都归了我;所以在南洋我还有香片茶吃。不过,这都是后话。我还得去找事。不远就是中华书局,好,就是中华书局吧。经理徐采明先生至今还是我的好朋友。倒不在乎他给找着个事作,他的人可爱。见了他,我说明来意。他说有办法。马上领我到华侨中学去。这个中学离街市至少有十多里,好在公众汽车(都是小而红的车,跑得飞快)方便,一会儿就到了。徐先生替我去吆喝。行了,他们正短个国文教员。马上搬来行李,上任大吉。有了事作,心才落了实,花两毛钱买了个大柚子吃吃。然后支了点钱,买了条毯子,因为夜间必须盖上的。买了身白衣裳,中不中,西不西,自有南洋风味。赊了部《辞源》;教书不同自己读书,字总得认清了——有好些好些字,我总以为认识而实在念不出。一夜睡得怪舒服;新《辞源》摆在桌上被老鼠啃坏,是美中不足。预备用皮鞋打老鼠,及至见了面,又不想多事了,老鼠的身量至少比《辞源》长,说不定还许是仙鼠呢,随它去吧。老鼠虽大,可并不多。许多是壁虎。到处是它们:棚上墙上玻璃杯里——敢情它们喜甜味,盛过汽水的杯子总有它们来照顾一下。它们还会唱,吱吱的,没什么好听,可也不十分讨厌。
天气是好的。早半天教书,很可以自自然然的,除非在堂上被学生问住,还不至于四脖子汗流的。吃过午饭就睡大觉,热便在暗中度过去。六点钟落太阳,晚饭后还可以作点工,壁虎在墙上唱着。夜间必须盖条毯子,可见是不热;比起南京的夏夜,这里简直是仙境了。我很得意,有薪水可拿,而夜间还可以盖毯子,美!况且还得冲凉呢,早午晚三次,在自来水龙头下,灌顶浇脊背,也是痛快事。
可是,住了不到几天,我发烧,身上起了小红点。平日我是很勇敢的,一病可就有点怕死。身上有小红点哟,这玩艺,痧疹归心,不死才怪!把校医请来了,他给了我两包金鸡纳霜,告诉我离死还很远。吃了金鸡纳霜,睡在床上,既然离死很远,死我也不怕了,于是依旧勇敢起来。早晚在床上听着户外行人的足声,“心眼”里制构着美的图画:路的两旁杂生着椰树槟榔;海蓝的天空;穿白或黑的女郎,赤着脚,趿拉着木板,嗒嗒的走,也许看一眼树丛中那怒红的花。有诗意呀。矮而黑的锡兰人,头缠着花布,一边走一边唱。躺了二天,颇能领略这种浓绿的浪漫味儿,病也就好了。
一下雨就更好了。雨来得快,止得快,沙沙的一阵,天又响晴。路上湿了,树木绿到不能再绿。空气里有些凉而浓厚的树林子味儿,马上可以穿上夹衣。喝碗热咖啡顶那个。
学校也很好。学生们都会听国语,大多数也能讲得很好。他们差不多都很活泼,因为下课后便不大穿衣,身上就黑黑的,健康色儿。他们都很爱中国,愿意听激烈的主张与言语。他们是资本家(大小不同,反正非有俩钱不能入学读书)的子弟,可是他们愿打倒资本家。对于文学,他们也爱最新的,自己也办文艺刊物的,他们对先生们不大有礼貌,可不是故意的;他们爽直。先生们若能和他们以诚相见,他们便很听话。可惜有的先生爱耍些小花样!学生们不奢华。一身白衣便解决了衣的问题;穿西服受洋罪的倒是先生们,因为先生们多是江浙与华北的人,多少习染了上海的派头儿。吃也简单,除了爱吃刨冰,他们并不多花钱。天气使衣食住都简单化了。以住说吧,有个床,有条毯子,便可以过去。没毯子,盖点报纸,其实也可以将就。再有个自来水管,作冲凉之用,便万事亨通。还有呢,社会是个工商社会,大家不讲究穿,不讲究排场,也不讲究什么作诗买书,所以学生自然能俭朴。从一方面说,这个地方没有上海或北平那样的文化;从另一方面说,它也没有酸味的文化病。此地不能产生《儒林外史》。自然,大烟窑子等是有的,可是学生还不至于干这些事儿。倒是由内地来的先生们觉得苦闷,没有社会。事业都在广东福建人手里,当教员的没有地位,也打不进广东或福建人的圈里去。教员似乎是一些高等工人,雇来的;出钱办学的人们没有把他们放在心里。玩的地方也没有,除了电影,没有可看的。所以住到三个月,我就有点厌烦了。别人也这么说。还拿天气说吧,老那么好,老那么好,没有变化,没有春夏秋冬,这就使人生厌。况且别的事儿也是死板板的没变化呢。学生们爱玩球,爱音乐,倒能有事可作。先生们在休息的时候,只能弄点汽水闲谈。我开始写《小坡的生日》。
三、《小坡的生日》
本来我想写部以南洋为背景的小说。我要表扬中国人开发南洋的功绩:树是我们栽的,田是我们垦的,房是我们盖的,路是我们修的,矿是我们开的。都是我们作的。毒蛇猛兽,荒林恶瘴,我们都不怕。我们赤手空拳打出一座南洋来。我要写这个。我们伟大。是的,现在西洋人立在我们头上。可是,事业还仗着我们。我们在西人之下,其他民族之上。假如南洋是个糖烧饼,我们是那个糖馅。我们可上可下。自要努力使劲,我们只有往上,不会退下。没有了我们,便没有了南洋,这是事实,自自然然的事实。马来人什么也不干,只会懒。印度人也干不过我们。西洋人住上三四年就得回家休息,不然便支持不住。干活是我们,作买卖是我们,行医当律师也是我们。住十年,百年,一千年,都可以,什么样的天气我们也受得住,什么样的苦我们也能吃,什么样的工作我们有能力去干。说手有手,说脑子有脑子。我要写这么一本小说。这不是英雄崇拜,而是民族崇拜。所谓民族崇拜,不是说某某先生会穿西装,讲外国话,和懂得怎样给太太提着小伞。我是要说这几百年来,光脚到南洋的那些真正好汉。没钱,没国家保护,什么也没有。硬去干,而且真干出玩艺来。我要写这些真正的中国人,真有劲的中国人。中国是他们的,南洋也是他们的。那些会提小伞的先生们,屁!连我也算在里面。
可是,我写不出。打算写,得到各处去游历。我没钱,没工夫。广东话,福建话,马来话,我都不会。不懂的事还很多很多。不敢动笔。黄曼士先生没事就带我去看各种事儿,为是供给我点材料。可是以几个月的工夫打算抓住一个地方的味儿,不会。再说呢,我必须描写海,和中国人怎样在海上冒险。对于海的知识太少了;我生在北方,到二十多岁才看见了轮船。
得补上一些。在到新加坡以前我还写过一本东西呢。在大陆上写了些,在由马赛到新加坡的船上写了些,一共写了四万多字。到了新加坡,我决定抛弃了它,书名是《大概如此》。
为什么中止了呢?慢慢的讲吧。这本书和《二马》差不多,也是写在伦敦的中国人。内容可是没有《二马》那么复杂,只有一男一女。男的穷而好学,女的富而遭了难。穷男人救了富女的,自然喽跟着就得恋爱。男的是真落于情海中,女的只拿爱作为一种应酬与报答,结果把男的毁了。文字写得并不错,可是我不满意这个题旨。设若我还住在欧洲,这本书一定能写完。
打了个大大的折扣,我开始写《小坡的生日》。我爱小孩,我注意小孩子们的行动。在新加坡,我虽没工夫去看成人的活动,可是街上跑来跑去的小孩,各种各色的小孩,是有意思的,可以随时看到的。下课之后,立在门口,就可以看到一两个中国的或马来的小儿在林边或路畔玩耍。好吧,我以小人儿们作主人翁来写出我所知道的南洋吧——恐怕是最小最小的那个南洋吧!
上半天完全消费在上课与改卷子上。下半天太热,非四点以后不能作什么。我只能在晚饭后写一点。一边写一边得驱逐蚊子,而老鼠与壁虎的捣乱也使我心中不甚太平,况且在热带的晚间独抱一灯,低着头写字,更仿佛有点说不过去:屋外的虫声,林中吹来的湿而微甜的晚风,道路上印度人的歌声,妇女们木板鞋的轻响,都使人觉得应到外边草地上去,卧看星天,永远不动一动。这地方的情调是热与软,它使人从心中觉到不应当作什么。我呢,一气写出一千字已极不容易,得把外间的一切都忘了才能把笔放在纸上。这需要极大的注意与努力,结果,写一千来字已是筋疲力尽,好似打过一次交手仗。朋友们稍微点点头,我就放下笔,随他们去到林边的一间门面的茶馆去喝咖啡了。从开始写直到离开此地,至少有四个整月,我一共才写成四万字,没法儿再快。
写《小坡的生日》的动机是:表面的写点新加坡的风景什么的。还有:以儿童为主,表现着弱小民族的联合——这是个理想,在事实上大家并不联合,单说广东与福建人中间的成见与争斗便很厉害。这本书没有一个白小孩,故意的落掉。写了三个多月吧,得到五万来字;到上海又补了一万。
这本书中好的地方,据我自己看,是言语的简单与那些像童话的部分。它不完全是童话,因为前半截有好些写实处——本来是要描写点真事。这么一来,实的地方太实,虚的地方又很虚,结果是既不像童话,又非以儿童为主的故事,有点四不像了。设若有工夫删改,把写实的部分去掉,或者还能成个东西。可是我没有这个工夫。顶可笑的是在南洋各色小孩都讲着漂亮(确是漂亮)的北平话。
《小坡的生日》写到五万来字,放年假了。我很不愿离开新加坡,可是要走这是个好时候,学期之末,正好结束。在这个时节,又有去作别的事情的机会。若是这些事情中有能成功的,我自然可以辞去教职而仍不离开此地,为是可以多得些经验。可是这些事都没成功,因为有人从中破坏。这么一来,我就决定离开。我不愿意自己的事和别人捣乱争吵。我已离家六年,老母已七十多岁,常有信催我回家。在阳历二月底,我又上了船。
在上海写完了,就手儿便把它交给了西谛,还在《小说月板》发表。登完,单行本已打好底版,被“一二八”的大火烧掉;所以才又交给生活书店印出来。
*********************************************************************************
老舍在狮城的足迹
2020-04-15 12:58 胡春来,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老舍在北京城的住家书房中写作
二度来新
1924年7月夏天,25岁的老舍从中国前往英国的航海途中,其乘坐的轮船暂时停靠在新加坡。老舍乐得有机会从红灯码头上岸,玩了一天,心中感觉非常惬意。可是因为只是暂时的停留,因此,老舍在时间紧迫之下,匆匆在大坡与小坡一带走了一回。他逗留最久的地点是位于桥南路172号的商务印书馆,一走进书店内,匆匆地大略看了一会儿,急急忙忙地买了一些中文书便返回轮船上去了。
▲新加坡旧年代桥南路的商务印书馆
从那一天起以后,老舍对新加坡意犹未尽,念念不忘南洋的风土人情。
5年后,1929年,老舍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5年的教学合约期满,原本打算回去中国。但他并不着急,计划先到法国巴黎游历3个月。他之所以有此想法,也许是当时他对于国内正处于“乱世”状态而心里存有芥蒂,回去了一时也不知如何面对。
游罢巴黎,老舍身上的洋元用得所剩无几,几乎无法回去中国,幸得巴黎的一些朋友为他筹集一点旅费,但也只够他买一张到新加坡的船票。不知是有意或是无意,老舍心里一直在惦记着5年前到过新加坡的情景,眼下既然旅费不足,索性就先到新加坡去,到了那儿再作打算。
其实,老舍之所以会二度来新,除了旅费的因素,另一个关键的因素是他在伦敦5年期间,阅读了一位英国著名小说家康拉德(Joseps Conrad)以南洋为题材撰写的小说而心动。尤其是康拉德的海洋小说与森林小说都写得非常精彩。比如康拉德的《裸命》等几部长篇小说中都有描写的台北城、婆罗洲、砂劳越、古晋、新加坡海港酒吧等场景,都使老舍非常向往南洋海域尤其是新加坡的岛国风情,心中一直等待机会再睹新加坡的异国风采。因此,在1929年10月秋天,老舍第二次来到新加坡,同样在红灯码头登陆。
老舍刚到新加坡的时候,接待他的人主要是南洋华侨中学的董事黄曼士先生。以后黄曼士就是与老舍在新加坡期间接触最多最亲近的朋友。
起初,老舍以受聘教员的身份入住在武吉知马路的南洋华侨中学校园内一座新盖好的单身教员宿舍虎豹楼里。后来,由于老舍跟黄曼士颇谈得来,于是,黄曼士索性把老舍接到自己的私宅里免费住宿,这样,两人可以天天见面,无所不谈。不过,奇怪的是,在后来的老舍南洋题材的作品中,却从未提及有关于黄曼士与他的故事。
▲接待老舍的新加坡富商兼书画收藏家黄曼士先生,热心与文人雅士交往
老舍非常感谢黄曼士对他的热诚接待,黄曼士不但协助他找到一份很适合的执教工作,还安排了一个理想的安身住所,一时之间让他解决了经济上的燃眉之急。
黄曼士的私宅位于武吉巴梳路,老舍个人对黄曼士先生和这条武吉巴梳路极生好感,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黄曼士不但是新加坡一名富商,也是新加坡著名书画收藏家,祖籍福州,自幼深受中华文化的熏陶,热爱书画古董等艺术品。除此之外,他还有一颗善良的心,凡因国内乱祸而南来避难者,他都私下给予庇护和提供栖身居所。老舍虽然不是避难而来,但黄曼士仰慕老舍是个文人作家,便与他交往。
由于资料上的缺欠,黃曼士的私宅在武吉巴梳(Bukit Pasoh Road)路段的哪一幢?至今无可考查了,只能估计它在离怡和轩俱乐部不远之处。以黄曼士喜欢结交文人雅士的个人品味来看,他的私宅应该是弥漫着淡雅恬静的氛围,而老舍则是看上黄曼士私宅有一座后花园。这里栽种的都是唯有南洋热带才可见到的花草植物,从后花园有时还可听到从怡和轩俱乐部或晋江会馆传来阵阵笛箫、二胡悠悠悦耳动听的乐曲。每逢佳节黄曼士都会邀请文人雅士到他府上雅聚,备餐吟诗赏花,这样优雅的环境,老舍的心情自然愉悦舒畅!
足迹所至
旅居新加坡5个月的南来作家老舍,平日除了教学、写作,他个人的活动范围并不广。据老舍的自述,他因为两次来新都是从红灯码头上岸的,所以,红灯码头给了他一个非常深刻的好印象。红灯码头不但是个抵境的口岸,周围的海洋景色和建筑物,在老舍眼里洋溢着狮城小岛与众不同的南洋特色。他说来到这里,就仿佛进入了康拉德小说中所描写的新加坡真实的场景里。其实,老舍喜欢欣赏红灯码头景色,也是为了心中一部小说寻找写作素材和灵感, 后来这部小说取名为《小坡的生日》。
另一个在老舍的印象中显得很有特色的地方,就是红灯码头对面的真者里(Change Alley)小巷市场。老舍第一次来新时就已发现真者里了,只是无奈没有机会游览。真者里小巷市场里,主要经营小买卖,市场里的商人除了华人之外,最多的是印度人、马来人、阿拉伯人等,他们依靠摆卖南洋特产谋生,有南洋草烟、香料、蔬菜水果类,比如榴梿、红毛丹、椰子、黄梨、芒果、香蕉、番薯、木薯等等,还有不同民族的服饰衣物、鞋子、生活器皿等等,叫老舍大开眼界。后来老舍都把这些南洋特色写进了《小坡的生日》小说中。
▲从浮尔顿广场上俯瞰的红灯码头,在旧年代的新加坡是一个很重要的抵境口岸,老舍两次在此登岸
除真者里市场外,老舍还游览了宏伟壮观的浮尔顿广场,也望见不远处的莱佛士大酒店,这些英殖民政府兴建的洋式建筑物,老舍在轮船上早已遥望到了,这可是让他心境驿动的景观!当时的红灯码头一带就是繁忙的商业区,周围街道上,洋人的马车、印度人的牛车、华人的人力车、三轮车来往穿梭,看在老舍眼里都是很有南洋特色的创作题材。同时,老舍也仿佛在验证康拉德小说中提及的这些新加坡景色,果然同如所见! 位于新加坡河口的浮尔顿大厦,大厦里的邮政总局,老舍就非常熟悉了,那是他常常来、必须要来的地方。因为当时要从新加坡寄回中国的家书,大多都是通过这里邮寄出去的,没有其他邮局可以办理。浮尔顿大厦几经周折,于1928年6月竣工,老舍第二次来新是1929年,这幢崭新的洋式庞大建筑物刚启用一年多而已。
老舍出国在外这么多年以来, 他的三部小说《老张的哲学》、《二马》、《赵子曰》都是在英国创作,然后寄回到中国去发表的,而老舍本身是殷切希望能够早日见到发表的作品,却无奈于当时的邮递服务速度费时与不便,无法如愿以偿。直到第二次来新加坡,某一回闲逛书局的时候,偶然发现在一份中国出版的《小说月报》上刊登了他最新创作的小说作品,他立马眼前亮,感觉这是一件多么有趣和令他感到意外、高兴的事啊!
老舍是新加坡植物园的常客,因为他在北京的住家原本就很喜欢种些花草植物怡情养性,来到新加坡,获悉有一个种类繁多的植物园,怎可错过呢?所以,每次游览植物园,都恋恋不舍。
老舍喜欢逛的书店就是位于桥南路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因为在这两家书店里可以买到来自中国、台湾、香港及本地出版的书刊。尤其是中华书局,对远离北京多年的老舍来说,在这里可以买到中国各地的出版物和稿纸、笔墨文具等,非常方便。当然,在商务印书馆里也同样可以买到他所需要的各类书刊。
校园生活
老舍经中华书局经理徐采明介绍,在南洋华侨中学得到一份工作,心中大为宽慰。一天老舍很高兴地花了两毛钱买了大柚子来吃,给自己庆祝,然后向学校预支点钱用来买一件白衣衫( 用来教课时穿的),但这白衣衫的款式不中不西的,却有南洋风味,他自觉很满意。自己再买一条小被单,因为夜晚睡觉总要盖被的。虽然天气比起北京好多了,但白天还是蛮热的,他一天要冲凉三次才舒服。
▲新加坡桥南路的中华书局
在狮城的老舍,花最多时间的地方,当然是他执教的南洋华侨中学的校园里。当时,老舍一天要执教几个小时的国文,月薪是叻币十余元。老舍负责教导的学生,年龄都在十五六岁左右。班里的这些学生,平时所讲的话,与作文里所写的内容很不一样,使老舍感到很惊讶!因为他发现一班十五六岁的学生的思想竟然如此激进,他们向老师提出的问题也特别多,这是与老舍在伦敦的教学有所不同的。在伦敦,老舍在东方学院华语系里担任华语讲师,主要是教导英国学生学习中华语言和官话,以及中国古典文学。相比之下,英国学生个性比较率直与成熟。虽然新加坡的学生外表有些肤浅,然而在言语、行为上“使我不敢笑他们”。因为五个多月的教课,让老舍察觉新加坡的学生的新思想偏向于东方,而非西方。或许,老舍认为新加坡的学生大多数来自富裕的家庭,他们除了读懂天下大事,其他的也不想了,若从外界接触了一些新思想,就紧紧的跟随着,不像伦敦中等阶级出身的学生,从不去思考天下大事。
所以,老舍在华侨中学执教后所得到的体验,让他有所领悟。他认为自己的新思想也跟着新加坡的学生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不能再回去像从前那样用狭隘的想法去写爱情小说了。而他所谓的新思想,即是新加坡的花园城市构想、多元种族的和谐社会。各种不同种族与宗教的小孩同在一起上课读书、玩乐,他感到很不可思议,但又很赞赏。唯有一事不解,在一起玩乐的孩子,当中不会有白种人的孩子。但这样已经很让老舍向往一个没有种族歧视、教育普及大众、人们的心朴实善良的文明社会。如此比较下,他终于明白华侨中学的学生新思想偏向于东方的原因了。于是,老舍打从心里决定日后回到祖国的时候,必须在学校教育政策上重新做一番思考和整顿。
心理纠结
▲老舍全家福1946年初摄于重庆北碚。(左起)妻子胡絜青、舒乙(后)、舒立(前)、老舍、舒雨、舒济
那老舍为何在华中教了5个月后就不干了?是自己辞职或是口头合约期满了?
在老舍的教学工作上,他是觉得学校环境很好,学生能听得懂他的国语,也能讲得一口很好的国语,性格好学活泼,情感上偏爱中国,思维上则喜欢一些激烈的、有争议性的时事问题与主张。虽然这些人生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却愿意打倒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他们对于文学,尤其是中国文学非常热爱。他们也主动办文艺刊物,这很合老舍之意。他感觉缺点就是对老师不是很有礼貌,然而与他们相处久了才知道这是一般学生的个性,并无恶意,混熟了,就可以谈笑风生。但是老舍个人认为,从内地过来当老师的人日子待久了都会渐渐觉得内心苦闷,因为新加坡这里的华人多数是南方移民的闽粤、潮汕人、海南、客家人,老舍是北京人,不会讲广东话、福建话、潮州话、马来话更不懂,不懂的事还有很多很多,总之北方人的生活习性是无法走入他们的心灵世界里去的。况且当个教员,社会地位不高,出钱办学的人也没有真正把他放在心里,所以平时的消遣除了看书看杂志看电影,逛街逛书局,也就没什么可玩的地方了。他住了三个月后开始苦闷、厌烦了,感觉连天气都是呆板的,没有春夏秋冬,没有风霜雨,生活有些无聊。于是开始创作他的《小坡的生日》。然而,由于新加坡的天气炎热,蚊子又多,有时屋里的老鼠和壁虎也出来捣乱,使他无法专心写作,每日写一千多字便觉得烦躁,索性跑去学校附近的咖啡店喝咖啡。
在咖啡店里喝咖啡反而使老舍缓解了烦躁的心情。因为这里可以听到中国妇女穿着木屐,走起路来嘀嘀嗒嗒的声响,这在北京城里是没有的。还有印度人的奶茶、印度歌曲,感觉仿佛身在西域,那种感觉不就是南洋风土民情了吗?开始写这部小说的时候, 老舍一直抱怨自己写不出什么东西。想出去走走,又要花钱,遇到街上的人,老舍又不会用南洋的方言跟他们说话,在沟通上有此障碍,所以只能叫黄曼士带他四处看看人家的生活,为小说寻找材料。老舍尤其特别注意小孩子们的生活行为,他们可以和不同的民族的同伴天真无邪地在街上跑来跑去,一个中国小孩与马来小孩在户外、街上奔跳玩耍,就是他所见到的南洋社群的生活,这些都是写入小说中的素材。
老舍在新加坡写了5万字的《小坡的生日》后便遇上学校放年假,心里想,到底回还是不回,甚是纠结。老舍是自认“我很不愿意离开新加坡,可是要走这是个好时候。”“我自然可以辞去教职而仍不离开此地,为的是可以多得些经验,可是这些事都没有成功,因为有人从中破坏。”至于他是被什么人从中破坏,他没有说个明白,只从他嘴里说“我不愿意自己的事和别人捣乱争吵。我已离家六年,老母已七十多岁,常有信催我回家。”于是,老舍在1930年2月底登上了回返中国的船,前往上海。回到上海之后,继续把《小坡的生日》补上一万多字才总算写完,发表在《小说月报》上。
老舍的个性和他的作品一样,爽朗、幽默、质朴、热情。他在狮城留下的足迹与身影,成为本地文坛上津津乐道的话题!
(作者为本地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