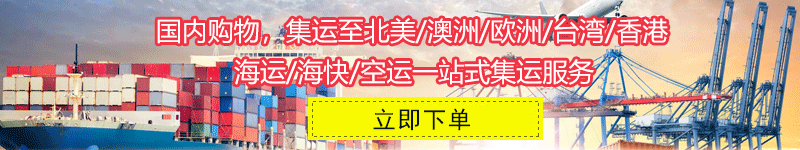原创 王哲 三明治
作者|王哲
我们来看这间五房式角头组屋,标价六十万。
漆了白色的大门敞开着,两三个老人坐在客厅的绿色转角沙发上说笑。大门里有个三平方米的不规则玄关,铺着绿色塑料假草皮。我太太侧过头看我一眼:她喜欢上这里了。
进客厅的房梁上有两个钩子,宜家的秋千摇摇摆摆,我立刻想象出两个儿子坐在上面笑闹的场景。
这里有家的氛围:十一楼、小玄关、大窗户、秋千、浅绿色布沙发,我们都喜欢。这会是我们老去的家——或只是第十三个过渡性住所?
接着看厨房、看几个房间,都是例行公事。我们其实都已经开始暗自计划:该怎么装修呢?我猜太太大概已经开始想装修的方案了。
这家的主人是空少、空姐,和阿公阿嬷住在一个屋檐下。面积大概一百五十平方米,装修得简洁,有四个房间,一个很大的客厅,还有别处少见的一整排半落地窗,窗框是全白的,透亮。只有卧室要重新装修,墙面刷白就行了.....我们俩没有多说什么,却想着同样的事:这值得我们安定下来,等孩子们长大成人。
熬到了在建屋局签字、拿钥匙的日子。根据新加坡建屋局的规定,需要确认组屋卖家在公积金帐户里是否有足够款项,不足的话则需要填补,否则就不能出售。正在电脑上查看资料的建屋局办公人员突然转向房主——那位英俊的空少——平淡地说:Sir,你的公积金差三万,要不要现在填补?然后转向我们:你们等他填补好了,就可以拿钥匙了.....房主面有难色,暗示我们出去谈。在大厅里,他告诉我们:“拿不出三万”。
“所以呢?”“所以,要么你们付,要么就不能卖了。”
像很多新移民一样,我们多多少少都遇到这种坐地起价的事。但是我们实在太想要这个组屋单位了....最后,我们出了两万元现金,等于房主多赚了两万,而我们拥有了可以终老于斯的好屋子。
那时候,我们不会预料到:九年以后,我太太竟然真的安息于此,安息在异乡、自己的屋子自己的床上。
这是我们的故事,新移民漂泊的普通故事。
初次租房
千禧年即将到来,我和一位大学同学通过了新加坡教育部的面试,成为教育部属下的合约教师。事实上,当时新加坡教育部也与中国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合作,通过汉办招聘中文教师,但我们并不知道这条官方管道,而是通过一家仲介公司,缴纳了上万元的仲介费,成功应聘入职。
从2000 年开始,每年大约有40 到70 名左右中国教师经过层层筛选和竞争,从近两万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通过汉办进入新加坡中小学(包括初级学院)任职;经过三年到六年,最终在新加坡生根的,大约每一批中只有15人左右。而像我这样,通过仲介公司投递简历,通过公开面试进入教育界的教师人数,则很难统计。官方招聘的教师,有些具备一定背景,能够优先获得招聘资讯,有些则是刚刚从师范大学毕业的学生。她们来到新加坡之后,有时会受到南洋理工大学教师进修学院的资深教师的“关照”,在衣食住行方面予以照顾。在社会阶层上占优势者,更能够获得优质资源——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中国特色”在新加坡的表现吧!
后来,我了解到:“汉办”的教师,在本地租房也能得到专业协助,但我的租房的经验却充满了戏剧性。
抵达新加坡的第一夜,我在多美歌的学生公寓栖身,那是仲介公司为前来就读语言学校和职业学校的学生租下的公寓单位。第二天一早,公司二当家Cindy 陪着我去北部三巴旺的组屋单位,据 Cindy 说,已经和屋主谈好了一间客房,月租金 300 元新币,那里靠近我被分配去的学校——胜宝旺中学。
十二月底的新加坡仍旧炎热。为了给屋主留下好印象,我特意穿上白色长袖衬衫、深蓝色长裤、皮鞋,有别于普通新加坡人的T 恤短裤人字拖。拖着两个行李箱,我和Cindy 从三巴旺地铁站走到不远处的组屋时,我早已满身湿透,衬衫长裤紧紧粘在身体上,但一想到很快就能安顿下来,我不免还是满怀期待。到了十楼的组屋单位门口,Cindy 出声招呼,一个高壮的中年男人现身,不耐烦地打量着我们。
Cindy 面带微笑:“Mr.Ho,昨天我们讲好了的,这是教育部招聘的王老师……”Cindy 在“教育部招聘”几个字上加重了声调,仿佛为了强调什么。中年男人一眼扫到我的行李箱:“他是哪里来的?中国来的?中国来的我不租,很臭的。”听到最后这句,Cindy 脸色也变了,她也是从福建来的新移民,不过她勉强忍住,连忙带着笑脸解释:“不是,Mr.Ho,王老师是教育部面试以后请的老师……”这位 Mr.Ho 却完全不再理会我们,转身进了房门,不再出现。
Cindy 满脸尴尬地安抚我,一边转身。这时我们注意到:这间组屋单位隔壁人家的门敞开着,一个老安娣(新加坡人称年老妇女 aunty)正坐在门口择菜叶。Cindy 蹲下去:“安娣,你们家有没有一间房要租?这是教育部请来的老师,要找一间房住,他在胜宝旺中学教书。”恐怕连Cindy 自己也没想到,这无可奈何的尝试竟然让我就以 300 元新币的月租,住进了我在新加坡的第一个“家”。
300 元的房间,是什么概念呢?面积大概 20 平方米,一张席梦思床垫,墙上有一个风扇,屋角有一塑胶的简易衣橱,但是有一个没有抽屉的四方桌子,可以放一叠作业和我的小铝锅。最棒的是有一扇很大的窗,隔着铁窗花能远眺街对面的绿色丛林。这是我的第一个落脚之处,经过了戏剧性的转折,我在这片陌生的南洋,暂时有了自己的一方空间。安娣说,可以用厨房,但是不能炒菜,只能煮汤——所以我先用小铝锅烧饭,然后把饭装在锅盖里;再用自己带来的几块咸肉,配上超市买的冬瓜煮成汤,配上白饭,这就是一顿很棒的晚餐了!这样的晚餐,支撑了我在新加坡的前两个星期。
在新加坡生活久了,我也许能够理解当初 Mr.Ho 对中国人的敌视,那里面包含着鄙视,但更多的,也许是对中国人来“抢饭碗”的恐惧,以及由此而生的厌恶。虽然,Mr.Ho 和他的母亲——那位收留我的安娣(是的,他们是母子)——一样,都是说“华文”的南来华人的后代。
年度搬迁
不久之后,我太太来新加坡,我们重新团聚了。她来了之后,我们退了那间小客房,以500 元的价格租下了安娣家里的主人房。和客房相比,主人房有独立厕所、窗外有晾衣杆、房间也大了一倍,有一个比较大的木头衣橱。我们的家当渐渐多了起来,两个箱子显然是不够的,于是,我们也渐渐开始添置一点小家具,日子一点点饱满起来。
电视直播“911”事件的那个傍晚,我刚好走过安娣家的客厅,飞机直直撞进世贸中心北塔的画面瞬间演变成一种真实的恐惧。那个著名的画面之后无数次在媒体上被直播,但是在那个下午,并没有人知晓它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深远影响。
从 2001 年到 2004 年,我们每年都会搬一次家。搬家的原因包括但不限于:房东要涨价、合租的房客要搬走、地点太靠近学校所以太吵、房东要收回房子自己住,等等。我们住遍了三巴旺地区的东南西北不同方位,申请了六次永久居民,才终于等来了一封厚厚的移民厅公函。当时的坊间传言各种各样:上半年申请比较容易成功、要有了男孩比较容易成功(将来可以服兵役)、成为永久教师比较容易成功、薪水高比较容易成功……这些都市传言无法证实,毕竟,ICA (移民厅)从来不会解释拒绝的真实原因;只有一则传言是真的——收到厚厚的移民厅公函,准是好事,因为里面是一大堆要填的表格;而要填表,就是申请成功了。
来到新加坡的第五年,我们终于拿到了新加坡共和国的永久居民权,而那真的就是一张淡绿色的卡片(绿卡)。拿到绿卡,对于大多数外国人来说,都意味着一件事:可以买房了!不用再为房东打工了!这是我们努力申请的动力啊!我们怀揣着幸福的绿卡,到处看房,到处梦想,恨不得见人就把绿卡掏出来展示一下:看看,看看,终于拿到了!我们也是新加坡的一份子了!我们早就厌倦了在三巴旺搬迁的日子,于是迅速选定了在附近的市镇义顺的房子。
义顺离三巴旺很近,我们自己的家也很静。屋子在七楼,开门就面对着义顺湖,楼边都是高大的树丛;虽然不是所谓的角头房(走廊尽头的角落,没有邻居的单位),但是只有一个邻居,而且邻居是马来西亚人,常年不住在新加坡。这间房的前主人,装修时用了传统的小格实木地板,打磨了一下再上漆,扎实又舒服,一股浓浓的南洋味道。这种旧式组屋的厨房也很宽大,我们的料理台足有三米长,每个週末,我的午后工作就是清洗料理台、打蜡、磨光……客居新加坡五年来,这是我们真正的第一个安身之处。我们的家当,从两口旅行箱,成长为一个居所,以及里面各种各样的锅碗瓢盆、书本唱片、橱柜桌椅,还有我们对未来的一些狂想。
每一个来到新加坡的移民,终极梦想都围绕着住房来展开。毕竟,这是一个以“居者有其屋”作为基本国策的都市国家。有住房,意味着我们被认可成为这个国家的一个部分,意味着不需要漂泊,意味着生活条件再差至少能出租房间来自救,也意味着一棵树开始生出了根。移民的过程是痛苦的,一位朋友曾经问我:“你见过一棵树把自己拔起来,移到别的地方去吗?”树被拔起来,那些根吱吱呀呀脱离母体的过程,像极了我们把自己从原本的社会结构中拔出来的过程;而一棵新种下的树,要摸索土壤的酸硷度、要试探著向深处搜寻水源,正如我们需要在新加坡建立人际关係、找寻自己的声音、丰盈自己的生活一样,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
没有哪个移民不曾心中纠结。
没有哪个移民不曾回头眷恋。
第一个孩子
拥有了义顺环路的这间四房式组屋,我们的心终于安定下来。之前的生活中,搬迁是我们生活的主轴;现在,结发十年,我们终于开始考虑生育后代。
其实,我们曾经打算做丁克族,觉得那样的生活方式挺符合我们的心愿。但随着年龄稍长,尤其是在异乡拥有了自己的房子,仿佛有了一个可以长久住下去的理由,更仿佛是未来有了某种保障,我们不由自主地回想起从小被灌输的想法来:养儿防老、孝顺父母、三代同堂、膝下犹虚……一时间觉得:安定下来,就该赶快生养啊!
不久,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开始孕育。太太孕吐得翻江倒海,我们自然联想到一定是食物不合口味,对家乡的思念具体化成了:对排骨年糕的思念、对黄鱼面的思念、对醃笃鲜的思念、对咸菜毛豆的思念,于是我们商量决定:送太太回国静养,等她生产时我再请假回国。这不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毕竟我们都还是持有中国护照,而“回家”这个词仿佛有着某种魔力,让我们抱着无限的乐观。
后来,我太太在国内看中了一个新加坡风格的公寓,并勇敢地(还是颇有远见?)贷款一百五十万,购置了一套房子,她决定:在那里迎接我们的一个孩子。
我们的大折腾开始了。
有了孩子,太太自然不方便再来新加坡,我的心也自然而然地偏向了回国。我们曾经那么热切地期待留在这个热带岛国,宁愿蜗居五年也要换来一张绿卡,现在却被回家这个执念占据了头脑。2005 年底,我卖掉了曾经那么心爱的宁静的义顺环路组屋,打包了全部重要家当,包括我的全套音响、一千张唱片,还有日渐增加的各种回忆,告别了在新加坡的朋友和我的学生们,回到了上海。
一次又一次的搬迁,背后的动机各不相同,但从形态上来看,真像候鸟,冬季、夏季、南下、北归,追逐着自己心目中的家园。我们这些移民,心中对于“家”的定义是犹疑不决的,有时候我们觉得“梁园虽好,非久留之地”,有时候,我们又满怀意气地“大丈夫四海为家”,其实我们自己也只不过在一次又一次地搬迁中增添了许多的包袱和牵挂。搬迁,并不是现代性的产物,但是现代性强化了迁移的可能性,有了海运空运,搬迁变得方便了,但每一次搬迁,都要丧失一些、再添补一些。
那时,尚年轻的我们并不知道:在搬迁过程中丧失的,其实不可能再找回,即便是得到的新环境,也不能弥补我们所丧失的细碎。
回到上海,依靠母亲在教育界的关系,我觅得了一份在私立高中担任教务主任的工作,薪水比起在新加坡时自然少了很多,日常所面对的尽是各种“中国式”的人际关系。在学校里,一群精明之极的退休教师和更精明的投资学校的董事长彼此角力;在家里,父母和丈人一家的关系需要努力平衡;在日常生活里,各种琐事无不穿插着中国式的斗智斗勇。这样的时刻,我和太太回忆起新加坡的生活,不由感叹那种生活方式的简单纯粹;新年红包只要两元,拜年只要提着两个橘子;人与人之间保持著“客气的冷漠”,不需要烦恼人情往还……离得远了,事物看起来总是更美好一点;不戴眼镜的时候,朦胧美总是让人倾心。大概就是出于这样的心理,有一天,太太提出,这次她去应聘新加坡教育部的教师,我一点也不反对——而结果,她也顺畅地通过了面试。我们又要短暂分手了,不过这一回,她打前站,我留守大后方。
蜗居
2008 年,中国举办奥运,全世界人们涌向中国,我却逆向而行。这次,我带着不满三岁的大儿子,再度南飞。太太已经在新加坡取得教职,暂时在西部一所小学实习,为了尽量靠近学校,她租下了一间 15 平方米的组屋客房,我们一家三口就暂时蜗居于此。
新加坡西部裕廊岛是工业区,这里有许多来自孟加拉的客工。孟加拉客工和印度客工外貌差别很小,孟加拉客工肤色黑中隐隐透着青色;此外,男性孟加拉客工一起外出时,好朋友常常手牵手,仿佛闺蜜一般,这也算是和印度客工的一点不同;不过,他们都特别喜欢围在一起谈天说地喝啤酒,或许也是疏解思乡之情的一种方式。说起来,其实我们和这些客工也没什么区别,我们都是从异国他乡前来,为了挣一点钱寄回家去,或是回家买房——为了利益驱动的移民,大抵如是。只不过,对于我们这些政府雇员,有机会拿到绿卡,进一步取得公民权,从而成为新加坡人,这一点和客工有所区别。社会性的迁徙或是人口流动,基本上都是从相对贫穷的地区向相对富裕地区流动,在流动的过程中,一些人由于产生了文化上的认同感,从而选择定居,成为新的居民;另一些人由于客观条件或是自身意愿,选择返回或是进一步向其他地区流动,直到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环境。这个过程就构成了文化之间的碰撞和融合。事实上,新加坡本身就是一个“罗惹”(Rojak,大杂烩)文化的代表,华人、马来人、印度人、欧亚裔的文化混杂在一起,形成了这个文化大杂烩的现代国家。新移民要么主动适应,要么就只能生活在自己的小范围朋友圈里。
我们租住的是二楼的房间,每到週末,楼下就会聚集著一些客工,他们的聊天常常持续到深夜,响亮的笑声如在耳边,让我们难以入眠。加上房东自己经济条件有限,仅仅提供了一张中间凹陷的席梦思,一家三口挤在上面,局促难安,我和太太不由得常常想起义顺环路的幽静组屋、上海的三室两厅公寓,对自己的选择时常充满了怀疑。
2008 年似乎漫长得没有尽头。这一年,我在一所国际学校工作,名义上是教育总管,实际上是校长和教师之间的三明治。夹在不通英文的中方校长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教师之间,我时常觉得自己是人格分裂的,更多时候又是充满无力感。这种无比荒谬的感受,随着十一个月后我的辞职终于到了尾声。在离职前的最后一天,来自哥伦比亚、加拿大、纽西兰、英国、菲律宾的教师们请我在纽顿小贩中心一起用餐告别,但是那位来自北京的校长却躲在他凉爽的办公室内,没有出现。
国际学校仿佛就是新加坡的缩影,人们来自世界各地,在这个岛国相逢,彼此产生交集,如果你能说英文,就能与他们产生奇妙的互动;但如果只说中文,那你的生活圈子将会大大缩小。要融入,就要割舍掉自己身上的一些过于“中国”的部分,学会以新加坡人的口头语、新加坡的生活方式、新加坡式的穿着来填补那一部分。
放弃原本属于自己的一部分,这个过程就像树舍弃自己的一部分枝干,一定会疼痛,但是新的枝干终归会生长出来,最终还是会绿叶葱茏、低声吟唱。而在那之间,没有割舍的部分,一定就是最本质的部分、也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核心。
2008 年底,我太太被派往新加坡最东部市镇——白沙的一所小学;我也成功地通过面试,重回教育部属下的东部一所中学任教,我们实现了长久以来的愿望,在安静、临海的市镇“白沙”重新觅得了一处四房式组屋单位,这是我们在新加坡的第十二次搬迁。在这里,我们迎来了第二个孩子的诞生。
新加坡人
或许人们的传言是真的(有两个男孩的家庭比较容易入籍),或许只是时机到了,或许只是刚好我们满足了移民厅的条件,2011 年1 月,我们拿到了移民厅的公函,准许我们入籍新加坡,公函也一并列明了需要去移民厅办理入籍的手续和退出中国国籍的步骤。到了这个时刻,我们不再有选择和后退的空间,唯有前行。
新加坡的新移民入籍程序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全家在移民厅宣誓入籍、念信约。念信约时,我回想起十二年前的场景:第一次在胜宝旺中学的操场上,全校师生一起面对新加坡国旗念信约,右手握拳放在左边胸口——我不明就里地照做,一位老师悄悄凑过来,好心地提醒:“王老师,这是我们新加坡人的信约,你不用读哦!”那一瞬间,我想到“独在异乡为异客”,仿佛一堵透明的玻璃墙在周围竖立,一股说不出的、苦涩的、寄人篱下的味道在口腔里弥漫。一个轮回之后,我们终于入籍新加坡,从二十五岁走向三十岁的尾端,人生中最好的黄金岁月已经留在这片土地上,身边又多了两个孩子,今后的日子将会有着怎样的流向?我们没有答案。
入籍程式的第二部分,是在社区俱乐部的礼堂举行的。白沙(巴西立)社区今年入籍的“新”新加坡人都必须参加,社区领袖(也是我们这一区的议员)张志贤副总理为新移民颁发入籍证书。这个时刻,似乎预告着我们搬迁生涯终于告一段落。我们环视大厅,大约有近百个家庭出席,菲律宾人、印度人、华人、欧洲人……不同种族聚集在这里,彼此见证这个重要的时刻。一如新加坡的所有仪式,入籍仪式安排得极其细微,每家都会领到贴纸,一再确认姓名无误,工作人员会引导大家逐行移出,排队上台、领证、合影、下台、领取照片、回座——标准的新加坡式流程。
成为新加坡人,是我们人生的重大改变。这意味着,将来回中国,要反向申请签证;但是我们每年出国旅行,有了说走就走的自由;但也意味着,在行政上,我们与自己的母国、与自己的母文化之间,脐带被切断了——哪怕仅仅是象征性的。
有谁见过一棵树把自己连根拔起来,迁移到别处?我们被连根拔起时,还有多少泥土附着在我们的足上?除了乡音、除了食物、除了父母,还有多少印记,将会伴随着我们一生?
像我们这样的第一代移民,要完全融入新加坡社会,实际上多多少少会遇到一些“玻璃墙”。首先是语言,大陆移民的英语水准并不差,但是我们在大学里训练的美式口音,和大多数新加坡人不太一样,很多词语发音也不同;像我这样在大学里懒于学英语的学生,要如何把自己的思维转换为英语思维更是困难;我们不是福建人,听不懂也不会说福建话、广东话、客家方言,等于是和新加坡华人社会的主要方言都绝缘了,连买一杯茶是“Teh O”还是“Teh Kosong”都分不清;新加坡人口语中杂糅的各种马来语、印度语词汇,我们更是一窍不通,连别人说的粗话也听不懂。凡此种种,事实上都是看不见的“玻璃墙”。
其次是生活习惯。本地的食材和小贩中心的本土食物,对我们的味蕾并不友好,大多数新移民家庭都倾向在自己家里用餐,吃的还是家乡味道的煎炒煮炸,但是很多时鲜是没有的,只能以其他食材代替,比如春笋、野菜、鲫鱼……到了近几年,微信团购有了许多从中国空运的新鲜食材,我们才又吃上了醃笃鲜、春捲、爱媛橙和中国草鱼,我们的年夜饭菜谱也丰富了起来。
我们应该入乡随俗,接受本地食物吗?当然应该,不过人的一生,不都是在追寻年少时的滋味吗?或许,到了新移民第二代,他们的食物光谱,就远远比我们要宽广了吧!
此外,儿女教育也是一个挑战。来自大陆的新移民家庭多数“内卷”,这一点和新加坡人的“怕输”足以并列。但是,我们怎样教育下一代,怎样和他们/她们沟通,恐怕是每个移民家庭的巨大挑战。我的两个男孩,幼子十四岁,正准备踏入青春期,自认是标准的“新加坡制造”;长子十九岁,已经接到了入伍通知,开始考虑应该加入陆军还是新组建的数码防卫军,在军中,他将会结识自己一生的袍泽挚友。他们彼此之间用英文沟通,只有和我对话使用华文。虽然我尽量鼓励他们阅读一些华文书籍,但是我也知道,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英语将是他们一生的“优选语”。
我们这些新移民家庭的后代从小接受本地教育,自然而然地和所有本地学生形成一样的价值观,使用一样的语言。新移民家庭聚在一起时,最常看见的场景是:家长们操着中国口音,南腔北调地聊天,孩子们却不约而同地用新加坡式英语沟通。我们总是试图把自己的观念来灌输给孩子,但是对他们来说,“中国”——已经只是一个地理概念,一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生活的地方” ,他们和那片土地已经没有了情感联系,这才是每个移民家庭的父母心里巨大的缺口吧!
没有什么能够填补这个缺口。其实,也不需要填补,我们给了下一代不一样的人生,那就让他们沿着新加坡人的道路走下去吧!
离别
在新加坡,我接触到、也最熟悉的的群体主要新移民的教师群体。实际上很多人和我有着类似的经历,但是这个群体却很少真的被看见,因为我们大多数都属于中产阶层,自动被默认为薪水较高、职业稳定、能够很好地融入新加坡社会的群体。但其实,我观察到:很多人也非常困惑,非常纠结。我们总是像候鸟一样来来去去,不断迁徙。每当到了假期,我们要决定:是回中国看望老人,还是带孩子去旅行?如果回中国,又要回哪个城市?
这些年间,总有人受不了新加坡的气候、工作繁重,决定回国找工作重新开始;回国之后,却发现已经不能融入国内的生活,受不了国内的各种繁琐手续,最后又回来。
1999 年,我获得仲介公司的通知,决定来新加坡参加教育部面试,但是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摆在面前:要出国,需要有签证;要有签证,需要先有护照;而要有护照,需要有公司出借营业执照担保——一个普通人,怎么能找到一间公司愿意出借营业执照担保?为了一本护照和签证,我想尽了办法,
最后还是仲介公司帮我解决了。今年开始,中国和新加坡互免签证。2024 年 2 月,得益于互免签证和泰勒・斯威夫特新加坡演唱会(亚洲唯一网站),来新加坡的中国大陆旅客达到了空前的33 万人次。在街头巷尾、各种网红打卡点、滨海湾金沙,到处可以听见熟悉的中国口音。但是此刻的我,内心的话语却是“怎么这么多中国游客?”——不知不觉间,中国对于我,已经成为“异域”。在疫情中,因为母亲动手术,我回到中国,那种草木皆兵、风声鹤唳、严防死守的氛围,更让我觉得:这片土地上,我已经是一个外人。但是,如果有人问我:“你是新加坡人吗?”我恐怕也会稍做犹豫。毕竟,我不会说福建话、不会用福建话在咖啡店点Kopi O 或是Kopi Siew Dai、一开口免不了被德士司机问“你是中国哪里的” ,和大多数新加坡人缺乏“服兵役”的共同记忆——我真的能算“新加坡人”吗?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2023 年,和我一起共同生活了27 年的太太由于癌症离开了我们。我感觉到生命的一部分彻底丧失了,在我的心里永远留下一个巨大的空洞。这个空洞是我们27 年共同成长的回忆,是我们如同候鸟一样往来新中两地的回忆,是我们在新加坡从一间狭小客房开始、最后拥有自己的五房式组屋的经历,是我们十三次搬迁路上共同打包行李的辛苦,是我们一起养育两个孩子、赋予他们新加坡身份的过程,是我们如何在一无所有中重塑自己的人生历程。
在这些年间,迁移,最后变成我们生活的主题。即使我们这一代暂时稳定了,未来我们还要考虑父母的问题,毕竟他们很难跟随我们迁移。这些问题,我无法回答,我只能在心里默默告诉太太:我会带着孩子们向前走,带着微笑走下去。
在搬迁的过程中,我认识到:作为离散华人,最终,我们唯一能携带的行李——是我们的语言。这个认知,在我重新开始写诗以后,越来越清晰。因此,就让我以一小节诗作为结尾:
摇摆吧,摇摆,来我们倾倒的屋内,
尝试不恳求,也不希冀。
细节塑造完美的日子,
和橱窗里的圣诞球一样完美,但
我将会说:走吧?走吧
而你再也不回答。
原标题:《在新加坡寻找我们的家|三明治离散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