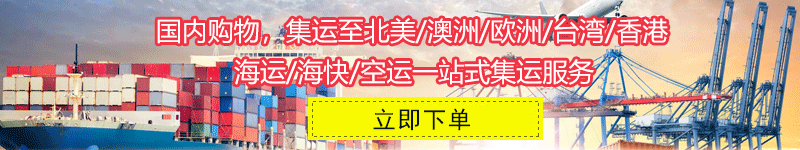文明”和“民族”概念的解构:从东南亚高地无政府主义历史谈起(逃避统治的艺术)书评
解构极端现代主义:从前现代国家发展中寻求启发:以人民的名义来反对个人,以程式化、扭曲化、精确静止的理念实现独裁统治。而这些理念背后反映出的统治者试图以极具说服力的现代工具和社会欲望为诱饵,强加于人民权威意识形态的行为,其实在无政府主义的抗争中就已经被解构了……
为了更好理解《逃避统治的艺术》一书在Scott学术研究中的地位,首先对他早期和晚期著作稍加梳理。
“弱者的武器”
其实只要从时间维度对斯科特的学术研究成果稍加梳理便能发现, Scott长期关注东南亚的小农群体,他们是历史叙事中的“无名者”,传统意义上的弱势群体,更是国家视角下征税、服役的对象,是国家的附庸。但通过对东南亚农民群体反抗行为的观察分析中,他使用了一系列至今仍被学界广泛使用的学理性概念,比如“弱者的武器”“隐藏文本”“逃避统治的艺术”,这些概念深入浅出,成为在底层抗争政治研究中里程碑式的学术成果。但“弱者的武器和隐藏文本”研究的是东南亚(马来西亚)农民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非公开的反抗行为,这类反抗包括偷懒、开小差、装糊涂、偷盗等形式。但应该注意,此类反抗逻辑的前提是农民仍然处在国家治理范畴以内,这使得后人普遍质疑其概念边界模糊,有人甚至嘲讽说,如果偷懒、开小差都可以被称为反抗,那我在上班时候打个喷嚏是不是也算对公司和老板的反抗?
极端现代主义
“……作为一种信仰,极端现代主义并非为某种政治倾向所独有:我们将会看到,左翼和右翼都有极端现代主义。第二个因素是毫无节制的滥用现代国家权力作为达到目标的工具。第三个因素是缺乏抵制这些计划能力的软弱和顺从的市民社会。极端现代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欲望,现代国家提供了实现欲望的工具,无能的市民社会则为建筑(反)乌托邦提供了平整的基础。”——Scott《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
19-20世纪以来,国家随着科技的发展而拥有了越来越强大的对自然和社会的征服和改造能力,但也在这种对秩序、社会改造和社会工程的盲目狂热之下,最终酿成让全世界为之战栗并付出惨重代价的种族大屠杀事件。二战之后,欧洲学者痛定思痛,掀起了对现代性和现代主义的反思与批判,在现代性与大屠杀的分析中,鲍曼在痛心又无奈地心情下直击寄希望于理性和科学技术实现完美社会构想的独裁本质。如果说鲍曼是从现代性“成功”地给世界带来灾难恶果的角度反思现代性,Scott在1998年《国家的视角》一书中则是从“极端现代主义”国家是如何“失败”地组织了若干曾令人为之自豪的“社会工程”的案例入手,阐释了现代国家是如何试图以人民之名义煽动社会对完美社会的渴望,借助现代化的科技和知识,却最终导致社会失控,历史传统、个体的尊严和价值被无视践踏的社会恶果。认为技术和理性并非万能,私人空间的信念、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私营部门和待议机构三因素是阻止极端现代主义的有效武器。
《逃避统治的艺术》:解构极端现代主义何以可能?——对前现代国家背景下无政府主义历史的思考
如果说,斯科特前期对农民反抗政治逻辑的研究尚不能信服于众,后期对极端现代主义的研究转向令人产生断裂突兀之感,那么斯科特在《逃避统治的艺术》一书中所做的努力及其成果是令人满意和赞叹的。在我看来,此书延续了Scott一贯的“发掘人们充满创造性的反抗政治逻辑,质疑国家组织形式”的学术立场,但这无疑是他在反抗国家研究中最精彩、最杂学、最具启示性的著作。正如杜赞奇在此书的推荐语中所写:“这部著作可能是迄今为止詹姆士·斯科特最重要的著作……这已经使他非常接近于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就是人们不仅可以逃避国家,而且可以避免国家形式本身。”
在此书中,Scott借助激进的建构主义的方法探讨了无政府主义历史何以可能的问题,进而实现深入理解前现代国家实质,解构文明、历史和文字等跟“国家”极具亲和性的概念的合理性的理论雄心。
但同时我们需要注意,即使Scott一直强调山地居民在逃避国家治理的历史过程中所具备的自主性、创造性和选择性,但在论述山地民族多重性、流动性、渗透性的认同现象时,他也承认自己采用了“激进的建构主义”这一分析方法,并认为“他们设计自己的身份认同,但却无法选择自己所处的客观环境”,也就是说山地民族看似“无限自由”的认同选择,实际上只是在面对相对稳定却强大的谷地国家时的策略选择,其一切策略均是相对于国家而言。可以打个比方来理解,国家是自变量,山地居民的策略选择是因变量,主动性掌握在自变量国家手中。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何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无政府的种族力量趋于消亡。
1、互生关系
Scott的研究发源于赞比亚这一横跨八个民族国家,多种族、多语言,存在诸多宗教传统、宇宙观的高地地区,凭借出色的史料搜集和梳理能力,他细致描述了此地两千年来长期存在的山地居民和谷地国家之间互生关系。
Scott认为赞比亚居民并非是谷底国家视角下的“活祖先”,“野蛮”未开化状态。赞比亚山地居民的以游离分散为特征的生存方式和社会结构并非是国家视角下的野蛮未开化,而是一种“自我野蛮化”,是逃避国家和抵御国家形式的自主的政治选择,这一观点被Scott在书中反复强调。为逃避和阻止国家的入侵,山地居民发展出了多层次的阻止国家的技术:包括低风险的地理空间的远离(从高度和距离两方面)、游耕、逃避的耕作以及混合类型农作物的选择(生存方式)、社会分裂和分散(平等自主离心式的社会结构)、以及口述传统(灵活可塑的历史谱系);以及高风险的叛乱,以及随之一致的先知宇宙观,在此基础上,作者发现尽管赞比亚山地居民反对谷底国家在政治上的统治,但双方却并非是完全隔离和对立的存在,双方已经形成了较为互补和稳定的经济交往关系,此外,谷底国家在人力、贵重商品和政治联盟三方面是依赖于山地居民的,从而出现了以物易物、猎奴的互动现象,在上述层面上两者是“共生关系”。
Ps (并非反对国家,而是逃避成为承担纳税、服役等沉重剥削的臣民,保持其政治自主性)
2、理解前现代国家景观及其本质
在本书中,前现代国家这一概念和农业国家相联系,即尚未出现现代交通、通讯工具,也没有发展出来机器工业生产。在本书中,前现代国家具有以下特征:
(1)构成单位具有流散性;具有流动性的单位构成王朝景观中相对持久的特征,国家是偶发的,国家是“依契约关联的复杂网络”,当国家分裂,系统中的单位会自动分裂出来保证自身的生存。
(2)“地形阻力”是其突出特点,国家形成地点、延展方向以及王权控制范围及其力度均受到地形因素影响。曼陀罗王国模型: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用不同照明强度的灯泡来代表统治者的个人魅力和统治力,灯泡越远越暗代表随着距离中心越来越远,不管精神的或世俗的权力都在逐渐削弱、
(3)帝国的想象:夸大的宇宙观和实际控制区域之间对比鲜明;其宇宙观的诉求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范围往往比实际控制的人力和谷物的范围大很多,意图将国家的“硬权力”和象征权力区别开。
(4)定居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以东南亚水稻国家为例,在此时期出现了对清晰、可统计、可监督的要求,为了更好纳税,需要对人口数量、分布和耕地情况有清晰的了解,从而实现纳税这一重要的国家需求,而变动的人口、多类型种植作物不利于国家的纳税行为。臣民——既是被纳入国家户籍管理,征税范围的固定地点的居民。
(5)作为财富资源的人口本质:人口和耕地结合制造财富,人力可形成军事力量,进而保护更有利可图的商贸安全;人口控制技术:奴隶制:战俘 猎奴 债务奴隶;财务人口;自我清算的国家空间:剥削居民—反抗和逃避的风险。虽然在不同时代背景,人口作用机制不同,但本质上人口都是增强国家实力的原始资源。涉及对人口的认识,就不得不提福柯在《安全领土与人口》中论述的治理术转变的根本性依据就是国家对人口概念的认识出现转变,即从对“人”的重视到对“人口”概念的重视;17世纪的重商主义传统之下,人口表明统治者力量,是国家和统治者力量的源泉、财富基础,对应的是政治规训机制,人口是需要服从法律的主体,这是一种从统治者和臣民的视角看人口;而在18世纪重农主义学派思想,人口不再被视为法律主体的集合,而是更强调其对统治者意志的服从,被视为一个整体,认为该主体具有自然性和规律性,应该运用统计学技术进行治理,而人口也不再与法律规范相对应,而开始把人口当做治理的技术,成为联结权力机制的重要一环,治理的目标是实现人口-财富的组合。
3、解构文明和野蛮——文明的退化是可能的,而且是一个政治范畴
文明化和未文明化构成了“半渗透膜”,人们可以在两侧穿来穿去。作者通过对山地居民的人口来源的分析可以发现,除了少数原始山地居民,多数是逃离的谷地农民、罪犯、异端教派、底层知识分子等,其实他们多是谷地居民的后人,因此,他们很可能曾经拥有过文字、定居种植水稻。因此,正如书中所写:“山地人群不再任何事情之前,他们应该被理解为之后,后灌溉水稻、后定居、后臣民、以及可能的后文字(关于他们文字是如何丢失的传说都指向谷地人的背叛和欺骗)。”由此可知,山地人和谷地人之间不仅有着密切的利益共生关系,而且山地人并非一直处于原始的未开化阶段,而是政治选择之后的后天结果,因此,野蛮文明、原始先进等对立概念其实更多是存在于人们的话语和意识之中,而非现实的存在。而这种针对山地人流动分散的生存状态的污名化其实是从国家视角来看的,与以“定居水稻种植、等级化、宗教信仰”为特征的国家状态相比,山地人“游耕采集、无首领、个人魅力型的先知”的各种以排斥国家为目的的社会结构特征自然受到排斥和憎恶。至此,作者完成了对“文明”话语的结构,文明的定义掌握在特定权力主体手中,文明的界限因差异的而存在和清晰因此野蛮山地人和文明谷地人其实是“国家居民”和“非国家居民”的差异。
4、文字的劣势和口述的优势;没有历史的优势
文字书写历史:书写和文本的世界不可避免的与国家联系在一起。识字和书写的技能被特层群体控制,文本内容体现了国家和权威意志,文字历史被固定延续下来,更多的是有助于剥削而非启蒙。
而对于无国家族群来说,适应、模仿和革新调整是重要的生存技能,因而口头和本地的文化具有强大吸引力,没有文字和书写的世界削弱了权力和知识的控制和死板,也就不利于某个权威、正统标准的谱系或历史的形成,人们的行为参照更 取决于哪一种更符合当前利益。而且口述具有更民主的特征:1 讲故事的能力普遍存在;2 口头文化具有无可取代的现场性,更能够表述其最初的意义,供人们自由选择,阻碍创新的阻力更小。
没有历史的优势:什么承载了历史,历史的作用?——国家视角来理解历史,进而理解为何无国家族群选择抛弃历史。
对于国家,“历史是构建群体关联,形塑群体认同,树立权威合法性的重要工具,”因此,丢弃历史,就是丢弃建立群体认同所需要的共同历史和谱系,这一选择看似弱化了群体集体抵御的可能性,但是使其适应纷乱喧嚣的能力达到最大。(书面和象征物品都可以承载历史:诗歌、碑匾、传说、谱系等,以及象征物品:徽章、印章、锣鼓等)
5、民族的想象力:先部落还是先国家?
赞比亚族群的认同策略选择:“基因、语言和观念的流动和交换密集且多方向,从而使任何试图通过完全清晰的一组地理 语言 生物或历史特征来区别和描述不同的族群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如同变色龙随着背景色改变颜色,模糊可变的认同具有保护价值。
山地民族认同是一种精心设计的政治手段来保证自己的族群在对权力和资源的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作者也提到,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族群和部落认同都和民族主义与国家独立的渴望(尽管经常失败)联系在一起。可以称作是“反国家的民族主义”
国家造就了部落:现有国家后有民族性;中国建国初期的民族界定工作?通过行政区域划分命名民族;汉族文明进化:生番、熟番、完全的臣民/进入版图(世界上最后的大圈地运动)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起落模式”:来描述印度尼西亚的荷兰政权凭空生成一个中国人的少数群体。身份认同的政治制度化通过改造社会生活的模式制造了再造族群的效果。
6、宗教:复活的先知
韦伯:“无特权阶级的宗教”:无特权的人希望通过激进的社会秩序重组获得利益,容易被承诺建立全新时代的运动和宗教吸引“犹太人50年解放的传统”“反转仪式”:东南亚的泼水节 天主教的狂欢节:短时间内的混乱无序,并非是为了宣泄紧张而建立的一个无害的安全阀而是使等级制度在一年内的其他时间可以更有效(P370)
韦伯认为,并非是贫困使得农民参加激进的宗教团体,而是因为他们即将失去独立小农的地位。同样山地发生的激烈的先知运动也是在其自主性受到国家威胁时发生。
山地人群也许在政治上不是谷底的下属,但他们积极参加了经济交换系统,甚至参加了世界性的观念 象征 宇宙观 称号 药方传说的循环传播。这是个对话 模仿和连接的过程。
魅力型领袖(先知):是地方上的世界主义者,其生活经验,知识文化跨越各地,进而通常扮演族群发言人的角色,从而在外界和村庄之间形成文化阻碍。
用户评论 查看更多>>
最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