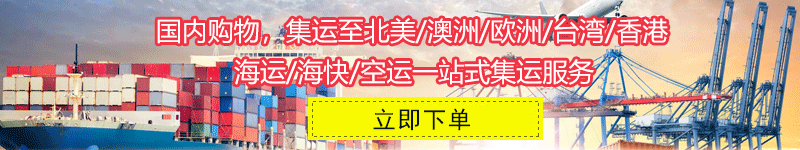符号的花园
在激荡而忙碌的当下,庭院是逃离喧嚣世界的象征。置身其中,哪怕是片刻的宁静,也足以让我们摆脱焦虑,吐纳升息;甚至只是单纯的想念,也足以让人思接千载,神入八荒。尽管庭院本身已经是“寄情山野,自由不羁”的符号,但如若我们能够跟随此书步入百花深处,必将沉醉于这片符号的花园,试图去理解美丽图像背后的无尽隐喻。
有两种方式能够展现庭院的力量:一种是宏大叙事,状如法式园林的规矩对称,宏伟旷达;而另一种则极尽精微,却又能寓意广大,日本庭院就充满了这样的趣味。如同各式禅宗公案的问答游戏,当我们要去亲近自然,日本庭院答非所问却让人醍醐灌顶。“比喻”这种禅宗妙法很早就被用于空间营造,比如作为禅宗祖庭的少林寺初祖庵,其外围墙裙碱石板上刻有一组连续的海漫石雕,形象地把整个建筑托在江海之上,以隐喻达摩一苇渡江,开创东土禅宗的伟业。无疑,日本庭院在“比喻”上更是青出于蓝,取材于岛国独特的自然环境,极尽抽象,形成充满寓意的符号花园。
时间
在飞鸟奈良时代(南北朝至初唐),先进的佛教文化从中国和朝鲜传入,伴随而来的是建筑技术的全面复刻,此时日本佛寺庭院类似于东土大唐,遍栽桃柳,以营造蓬莱之境,比喻仙道之所。
平安时代(中唐到北宋),日本产生了区别于中式寺庙、结合东瀛潮湿气候风土、更重华丽享乐的殿式府邸,其单体建筑以透廊连接,建筑和庭院相互渗透,融为一体。在这些被建筑、透廊和院墙围合的庭院中,开始产生了初具特色的日式景观。平安时代后期《作庭记》总结其立石要旨,不同于中式的“以石象山”,象征海景成为特色主题。从设计的角度出发,造园方法无非是回忆创作者所历名胜,用“以小见大”的象征手法将美景再现。立石像山,卧石似岛,于是日式“大海样”立石少而卧石多,比喻海上仙山,之后甚至以砂代水,产生抽象的、雕塑般的枯山水艺术。
平安时代后期,日本进入末法时代,战乱不停,社会动荡,人心不安。于是人们渴求极乐净土的平和感,象征净土的泉池园代替仙道庭院,成为悲怆时代的心灵寄寓。
在镰仓和室町时代(北宋末年,南宋到明初),日本出现幕府政权,引入禅宗思想,发扬武家文化。朴素简洁、庄严肃穆的书院造建筑往往辅以生机勃勃的泉池回游式庭院,可漫步其中,亦可坐观窗景。其后时代出现的龙安寺枯山水园和金阁寺、银阁寺池泉园为佳例。
及至战国和安土桃山时代(明代中晚期),豪华壮丽的天守阁城堡展现着乱世中的醉生梦死,庭院中的蓬莱仙洲象征人们渴望逃离现实的心灵挣扎。然而在战乱的紧张感中,人们不仅能逃往纸醉金迷的夸张幻境,也可以化繁为简,从容雅致,以“计白当黑”的禅宗思维走向相反的符号象征,终于成就了日本独特的数寄之风,寓意以优雅的方式追寻一方净土,远离纷争,寄情山水,隐遁山林……
空间
曾有诸多学者试图对日本建筑的独特性进行总结,阿瑟·德雷克斯勒(ArthurDrexler)1955年出版了《日本的建筑》,建筑师丹下健三、建筑评论家川添登、摄影师渡辺义雄1965年合著了《伊势—日本建筑的原型》,历史学家伊藤贞司、艺术家野口勇和摄影师二川幸夫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出版了《日本建筑的根源》,西井一夫和穂积和夫在1983年合著了《什么是日本建筑?》……尽管采用不同的分类方式,但他们都强调了日本空间的一个重要特征: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室内外的流动感。庭院和建筑的这种通透感产生于日本潮湿的气候和风土,也源自神道教“不可围合封闭土地”的神话寓言。一个典型的日本庭院中,围绕建筑的“缘侧”回廊是半露天的步道,作为墙壁的雨户围板可以取下,障子板(覆盖着半透明纸的木格屏)和袄(覆盖着不透明纸的木格屏)可以灵活开合,在顷刻间使庭院和室内融为一体,动静之变触动人心。
然而,这种通透感又并非是说一览无余,日文中的“透ける”一词,意为透过很薄的物体看到对面的事物。“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这种透明似乎更像是建筑家柯林罗所谓的“现象的透明”(通过建筑形式的重叠,表现出空间的深奥之感)而非物理性的透明。比如在书院造的房屋里,即便打开拉窗也只能“框景般”地看到庭院一半的景致;茶室被设计得几乎完全封闭,但鸟声树影又可以暧昧地融入室内。
于是,对于庭院来说,看似的劣势便可逆转为设计的优点,颇具禅宗意味。建筑场地的不规整反而利于形成曲折的围墙;凹凸的建筑单体可以产生变化的观景界面;曲折的透廊可以创造视觉深度;房间过大的进深被小天井破解……于是,仅仅在一处寺庙/宅邸中,便划分出诸多大小不一的庭院,成就了丰富的体验,如大门到玄关的通道庭院,步入茶室的茶庭露地,可游可坐观的数寄之园(泉池回游园),适宜坐观的小坪庭等(可以是抽象枯山水,也可以是植物搭配)。同样充满禅宗意味的逆转关系还体现在数寄屋的材质,貌似拙朴却构造精湛,造价昂贵……
终,这些空间和材质的特质都幻化为一种充满象征性的审美体验。以茶庭为例,让我们看看一个日本庭院空间如何构建起具体的符号世界。“福地洞天、壶中天地”是东亚文化关于文人居所的终极想象,茶室及其庭院正是要营造脱离俗世的隔绝之感。当我们在庭院中散步,在腰挂处休憩,在室内享受茶会,就会瞬间进入与世隔绝的精神状态。
首先,茶室的尺寸甚至被压缩为只能“促膝而坐”的四叠半(1叠约为1.65平方米)榻榻米大小,在其中饮茶仿佛是再现僧侣们面对达摩祖师像,共饮一杯茶的场景。这促狭的尺度和《维摩经》中的禅宗教义密不可分,相传维摩诘在同样大小的房间中迎接文殊菩萨及佛陀的八万四千名弟子,尽精微,致广大。
其次,茶室本身被设计为“空无一物”的抽象空间,除了在状如佛堂壁龛的“床之间”上摆放插花、水墨卷轴画,从地板到天花板,从茶具到服饰,室内所有的色调都偏向于淡素,让人专注于茶道仪式而不为环境所吸引。正如罗兰·巴尔特《符号帝国》所言,“符号的小屋”仿佛是一件能够移动的家具,没有座位,没有床,也没有桌子,和西方秩序井然的室内完全不同。但当空间失去了中心性,人们也就无从关注家具的秩序,人的身体成为空间的主体。
再次,辩证与残缺的美学感受弥漫于整个空间,煮水壶若是圆的,盛水的器皿需要有棱有角;茶碗若是黑色釉彩,茶叶罐便不可是黑色漆光;房间梁架的构成绝不可对称圆满,反而是去追求自由天然,不从于法度公式;经年陈旧、昏暗幽明的“寂”室内却必须保持清洁无尘;封闭的室内却需要“透”而不“开”,如同长谷川等伯雾气中错落有致的松林图,障子外的树影、阳光和鸟鸣还是会微弱地通过墙壁传入茶室,这种精微的自然氛围更强化了象征性的封闭世界……
人间
后,回到“人间”,在一座茶室中,关于隐喻的游戏并不止于器物或氛围,在异常寂静和澄明的促膝之地,伴着时而“随浪如花”、时而“暴雨滂沱”的如乐沸水,感受到对方的呼吸、表情、心绪是茶主和客人的必修之课,心灵的碰撞才是茶会动人心魄的想象力仪式。
于是,相反于寺庙的静观式庭院,茶庭故意不去营造供人静观的优美风景,反而会通过遮天蔽日的大树(尤其是在利休徒弟织部的设计中)、“透而不开”的围墙营造出深邃山林的意境。待合的休憩让客人平复心绪,在深邃的环境中听到寂静的远方;蹲踞洗手则让人具有蹲下的谦逊心情;在飞石路上经过,则不会因为营造的风景扰乱客人寻求茶道的决心;而低矮的躏口让人放下武器,弯腰进入……茶庭用一种人工加工的、却非如画的自然去引导身体的动作,但是正如人们看到关守石会踟蹰不前一样,唯有想象力才能真正成就游园的妙趣。
同样,无论是玄关通道庭院,可游可观的数寄之园,还是适宜坐观的小坪庭,都充满了符号的寓意却又有着因地制宜、不拘法度的形式,每个流派都有自己的造园规则,且同一个流派不同的造园家也会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设计。面对千变万化的庭院尺度、景观配置和细部构造,也许我们并不需要去区分“织部灯笼”和“雪见灯笼”的形制差异,然而它们的“比喻”世界让作为设计的“物”重回人间,符号的花园让我们重新感到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