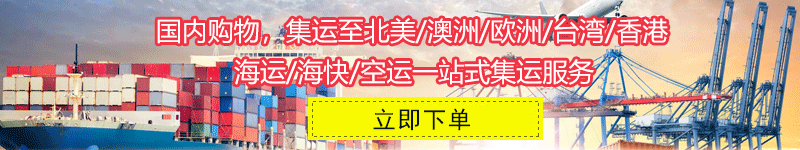文_ 周俊 图片_ 上坐家居
椅子,日本只有现代的。因为,在日本,甚至椅子本身就带着现代化的意味。
虽然,在日本被称为“正坐”的跪坐姿势——上身挺直、膝盖着地、臀部靠在脚后跟上——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但是,在唐代逐渐接受“胡床”这一高足坐具后,日本似乎从未打算改变。在远东的这个岛国,榻榻米承担了椅子、桌子、沙发、床的所有功能,人们晚上在榻榻米上睡觉,白天把被褥收起,在上面用餐、喝茶、安居。直至明治维新,作为欧美生活、进步文明的象征,椅子才开始登其堂,入其室。
昭和十一年(1936),柳宗悦在新建好的家里,围着餐桌摆了几张英国的老椅子。
和这座柳氏私宅一起修建的还有它东侧的民艺馆——在柳宗悦发起十年后,日本民艺运动终于有了自己的展馆,容纳柳宗悦和其他倡导者从四处搜集来的民艺品。食器、家具、人偶、服饰——柳宗悦从这些日常用品中发现了生活之美。
在其著作中,柳宗悦这样定义民艺品:第一,是实用品,第二,由无名职人制作,第三,是大众用品,批量制造,价格便宜,贴近人们生活。
他并不认同当时流行的西方艺术观,比起当时受到尊崇的鉴赏用的艺术品,他觉得生活中实用而温暖的器物更有美感。“所谓美,归根到底是与‘自心在’相关联的。禅语说:‘求美则不得美,不求美则美矣’。这意味着现代艺术被变形所拘束时,反而会远离自在。”研究过康德,翻译过许多西方著作的柳宗悦还是更加认同禅宗的观念。
那些英国18世纪的老椅子就是柳宗悦所喜欢的民艺品之一。民艺运动的推行者黑田辰秋、浜田庄司等人,常常坐在它上面,高谈阔论生活器物之美。
显然,这种实用美学后来也成为影响他长子柳宗理以及几代日本设计师的重要思想,不过那是后话了。这时的柳宗理刚从大学毕业,他迷上的是当时正兴盛的西方现代主义设计,尤其是其中肯定机器生产,赞赏新技术、新材料的包豪斯和倡导“没有装饰,就是最棒的装饰”的柯布西耶。
甚至在柳宗理被突然征召去战场时,身上只带的一本《光辉城市》就是柯布西耶的作品,“心想既然要死的话,至少要跟柯布西耶一起死”。“可它不是很重吗?”有记者问。“所以,后来受不了了,我只好把它埋在菲律宾的丛林里。”2000年,85岁的柳宗理在回忆起这件事时还露出种狡黠的孩童似的神情。
书埋在了菲律宾,柳宗理也没有死。在1940年,他还成了柯布西耶事务所设计师夏洛特·贝里安访问日本时的助理。在日本,贝里安用日本传统家具材料设计制作出现代家具与现代工艺美术作品,并举办了名为“传统、选择、创新”的展览。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展览触动了使用着黑田辰秋的桌子、芹泽銈介的拉门用纸、浜田庄司的壶碗长大的柳宗理。
几年后,他设计出将传统民艺之美用现代机械技术重现的作品——“蝴蝶椅”,被称为日本工业设计的第一人。
虽然严格来说,蝴蝶椅其实是一把小凳子。设计时,柳宗理用的是一种刚听说的新技术——曲线形模铸胶合板,这种技术刚刚用在复健器材上不久。
他用塑胶片模型将两片结构相同、造型优美的曲面合板通过一个铁杆装置,反向对称地连接在一起。新创造的不同寻常的椅子结构,让它看起来既像一只灵动展翅的蝴蝶,又像日本传统建筑里结实的拱门,又轻又稳。
不过,由于曲面工艺复杂,这个柳宗理手里优美的模型找到能将它真正幻化成蝶的制作者还有好几年。
不过那时,原本和日本无缘的椅子正在从工作场合逐渐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刚结束的二战毁灭了不少日本人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人们大批离开乡村,涌入都市,工作似乎成为唯一的身份与寄托。这在带来了战后日本经济迅速恢复的同时,也带走了人们复原生活方式的能力。
房间是铺木地板还是草席?是使用被褥还是使用床?是设计榻榻米还是桌椅?是使用纸拉窗还是窗帘?人们再没有精力对这些东西一一确认。在“欧美梦”和父辈的习惯之间,似乎大多数人选择的是“都放那吧”:既将有着榻榻米和坐垫的和式房间保留,又在另一个房间铺着木地板放上沙发、桌椅和床,有些家庭则干脆直接在榻榻米上放上沙发和茶几。
制造这些的日本家具界则在一边跟风似地模仿欧美产品,一边勤力地消化新学到的现代制造技术。
在这股混乱又兴奋的潮流中,柳宗理拿着蝴蝶椅模型在和研究合板的匠人商量。研究了五年,又开发了两年,在现代企业的匠人手中,一片片仅1mm 的薄木片,在高温下以高压结合,再压模成型、修饰,成就了蝴蝶椅不可思议的立体曲线——蝴蝶椅面世之时,正好是民艺运动发起30 年。
1957 年,在米兰三年展上,来自亚洲的蝴蝶椅斩获金奖,之后又被美国MoMA现代美术馆永久收藏,这被视作现代技术与东方传统结合的里程碑。
里程碑的意思是,某一段路要结束了,另一段路要开始了。
同样在1957 年,日本各大百货公司接受日本工业设计协会的建议,设置“G”(Good Design)标志奖,从人性、真实、创造、魅力、伦理角度评选出好的设计,给予“G”标志。这个奖现在还在颁发,而且成为日本上世纪60 年代进入艺术设计全盛时期后的重要推动力量。
牛津大学人类学博士奈尼尔•巴利曾在《天真的人类学家》中这样写道:“有一天,我与烟草店老板一起外出吃饭,不知为什么,突然幸福感紧紧包围我,后来我才发现我坐的是布套扶手椅。在多瓦悠兰,我不是坐在石头上,便是坐酋长的摇摇欲坠的折叠椅或者教会的硬背椅,这是数个月来我第一次坐到扶手椅。”我原以为,只有走到人类社会的源头处才会有这样的体验:椅子从来都不只是椅子。
可是,抛掉纸上的阅读与观看,来到北京曾经的皇家粮仓所在地,参观名为“上坐之美”的日本家具体验展时,我忽然也想到了这句话。
在那个历时六百年、储藏皇粮和俸米的古老仓库,柳宗理的椅子,连同他其他的日本设计师同行——川上元美、原研哉、奥山清行、佐佐木敏光的作品,安安静静地放置在一起。
川上元美的扶手椅是2012年“G”标志奖的获得者,和它的设计者一样,乍一看,它也长了一张冷峻瘦削的脸。
川上元美是继柳宗理之后,将日本现代家具推向国际的产品设计师。这位今年七十四岁的老绅士几乎永远都将衬衫扣到第一颗纽扣,露出像被削过一样的侧脸线条。
他设计的扶手椅有着宽大的坐面和靠背,扶手和椅子后腿巧妙地融为一体,腿部自上而下的瘦削线条透出一种骨干与冷峻。仔细去看,你才能发现这款椅子实际的“温柔”:椅背和扶手连接处都用了圆弧处理,贴合人体曲线,也中和了椅子本身过于现代化的几何感;而它瘦削的腿部也并非毫无意义的装饰设计——它不仅减轻了这款实木椅子的重量,让它方便移动,而且可以上下叠放,这在木制座椅中尤为罕见。
(万物有灵论的潜在影响,促使很多日本设计师在选择材料时会抱着一种恭敬的心态,尤其在对待木头上,更是遵循“道法自然”的原则,使设计最大程度符合木材自身的特
性。柳宗理的“柳氏靠背椅”(左)和川上元美的玄关凳(右)都体现了这一做法。)
他另外一款玄关凳同样毫无痕迹地将现代化功能主义和日本设计美感相结合。
这款凳子显著之处是它的功能性:把日本人穿鞋时常用到的鞋拔子插在凳子上,与之融为一体。它的设计美感是隐蔽的,只有使用时你才会发现,鞋拔子并非和插孔完全贴合,每一次使用后,它都会像钟摆一样产生有规律的摇动。反正,那意外的灵动带来的欣喜让我爱上了这位老是在照片中不苟言笑的男人。柳宗理的“蝴蝶椅”完美的线条只停留在二维的照片中,当天他另一款椅子的曲线将我空无的想像填满了。
这是一把“飞驒产业”在2007年复刻生产的“柳氏靠背椅”。椅子采用坚硬的橡木制成,圆盘似的坐面被造型独特的锥形凳脚托起来。亮点是它用单根曲木做出来的靠背,这是我好不容易想出来的比喻“浑圆的形状就像一个拙朴又温暖的拥抱”。
然后就理解了小他40岁的著名家具设计师深泽直人为何会那么崇拜他。那是“滑出来的线条”,用深泽直人的话说。它不同于电脑上画出来的无比流畅的抛物线——那是被化为符号后的曲线,是无数常数的集合,可以化为数列,更改常数就可以随意调整线条——而是人手所创造的曲线,混杂了二次元跟三次元的线条,极端复杂,“柳宗理的线条更是独特得让人怎么想也想不清。”
这和柳宗理的设计习惯有关。他很少画设计图,在创作时,都会先用纸、飞机木(易于切割的木头)、保丽龙、石膏等来摸索造型,做出雏形来模拟形体,接着试作,一边确认顺手与否、形体、重量的平衡感等问题,一边修正。等到所有的试做都没有问题后才会画成图说。既然“是手要使用的东西,所以当然要用手来设计”,“用手去感受,手上便会有答案”。
而且私以为,这种对曲线之美的极度敏感实在很难出现第二人。
毕竟,用柳宗理自己的话来说,“我家里的用的东西大概没有坏的设计,据说我小时候曾人小鬼大地评价过,“这个碗不错”——这个碗要么是浜田庄司,要么是伯纳·李奇(Bernard Leach)的。”
(原研哉算得上是日本中生代国际级的平面设计大师。作为无印良品的艺术总监,他有着很多国际设计师无法避免的喜好:设计一把椅子。与包豪斯风格影响下的西方同行明显不同,他设计的“叠坐”具有浓重的日式风格。)
与其他几位设计师不同,直到不幸早逝,佐佐木敏光都没有搬离自己的出生地——大分县日田市。在这座有着悠久农业发展史的乡村里,享受着童年起就有的美丽景物:春天一望无际,犹如黄色茵褥般的菜花田,夏天火烧云点染着的殷红色天空,秋天,漫山遍野的红叶里野生的山栗子和野葡萄。在为他而写的一篇朋友的讣文里,那位同样是设计师的朋友赞叹他“在乡村里,做出了世界级的设计”。
在日本的设计中一直有着崇敬自然的思想。日本最普遍的神道文化认为神是无所不在的,这种思想逐渐演变成万物有灵的人生观。当工匠制作器物期间未能顺乎材料的本质而导致大量的浪费时,其师傅必然会要求他向这些材料深深地鞠一躬,以示对物灵的歉意。
山城长大的佐佐木尤其懂得珍惜自然之美。除了追求造型上的自然,佐佐木决定尝试使用更质朴的材料。他决定挑战家具的规则——去除树节,选取直木——为什么要将大自然的丰富表情抹成统一的样子呢?
“禅是一种拒绝,它拒绝所有的刻意和伪装。”佐佐木说。
在他推出的“森之语”系列中,树干的年轮、木纹、木节,这些来自森林的信息,都没有掩盖地出现在了家具上,“要让人们认识到森林资源的减少等环境问题”。
他的禅意还表现在造型上,“森之语”系列沙发有着又宽又平的坐面,可以铺上柔软的沙发垫,也可以直接盘坐于木质坐面。旁边扶手也是宽平设计,与其说是扶手,更像个简单的边桌。整个造型的低矮也更符合东方人的身高,坐下后让人心生平静。
生于1915 年的柳宗理有一辆三菱Willys吉普车,开了50 多年,驾驶座因为生锈而被换过三次,直到80多岁被家人禁止开车才停止使用。在柳宗理眼里,让产品活得久一点,让它不会过时是设计师的使命,“制造出一大堆垃圾,说不定是设计者的最大罪行。”
实际上,日本的汽车设计师,同样难以面对自己的设计成为工业垃圾。奥山清行,设计过法拉利传奇车型ENZO、马莎拉蒂BirdCage 75th 梦之车的他,每次回老家总会去看附近一个由废旧汽车堆满的山坡。
“其中确实曾有我设计的车”,在NHK拍的纪录片里,他看着满坡的汽车残骸说这句话时黯然苦笑了一下。“又气愤,又难过,有对他人的怨气,也有对自己的忿恨,是种百感交集、非常复杂的心情。没有浸入感情制作的东西的结局大概就是这样,也许因为这种东西不具有能够传递的情感吧。如果制造者不注入感情的话,残骸也好,新车也好,都是无法打动人的。”
不知道和这有没有关系,他最近也推出了自己的家具设计,在“上坐”展出的是他和飞驒合作的“清行系列”。这款坐垫为红色的椅子还真让人联想到未来感的外形的法拉ENZO。椅背采用一整件曲木制作,与椅足的楔形曲线相呼应。桌腿的菱形线条,锐利、硬朗,呈现出日本设计里少有的力量感。这款椅子使用的是压缩杉面板技术,通过干燥、压缩技术及桌板拼接技术的开发增加杉木密度,解决它过于柔软,不适合家具制作的问题。当杉木的特有香气和这款锋锐气质的椅子结合起来时,竟让我有自然与科技结合之感。
(川上元美的扶手椅,扶手与后腿融为一体,瘦削而冷峻,就如她的设计者——另一位将日本现代家具推向国际的产品设计师瘦削而冷峻的面容。)
而像很多日本人一样,原研哉即使家里添置了椅子沙发,仍然习惯坐在榻榻米上,“就算沙发在旁边,也会被当成靠垫”,说到这时,这个日本中生代国际级设计大师、无印良品设计总监羞涩地笑了一下。
他这样解释自己对榻榻米的独爱:“坐着视线很低,让人很平静。”
在他的小书斋里,只有一张矮桌和书架。“下面可以像暖炕一样把脚伸进去,坐在垫子上将腿置入,仿佛自己的座舱”,最近,偶尔也会坐累,他便想着给自己设计一个没有凳腿的座椅给腰部做支撑。
其实,他设计的哪是椅子,简直像直接将空心圆折叠起来,在空中用线画出来的一方“坐”的空间。
这种空灵的设计需要精巧曲木工艺来实现它。据说,为兼顾线条的流畅与使用上的牢固,这把叠座由六截小段曲木榫接而成。纹理上拼接得严丝合缝,每一段的弧度都打磨得圆润光滑,而且用的并非均匀单一的线条,在每一段弧度转折的细节中,似乎都藏着书法运笔里的劲道——勒、弩、策、掠、啄,无处不精到。
正是原研哉在空气里圈出的精细空白,让我想起了奈尼尔•巴利的话,如果他看到这把椅子,是不是会和我生出一样的感慨:至此,人类真的太富有了。直接坐在地上,和使用一把近乎无用的椅子坐在地上,人脑的沟壑到底走了多远。
简单,和复杂的简单。空无,和富有的空无,日本设计师又到底走了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