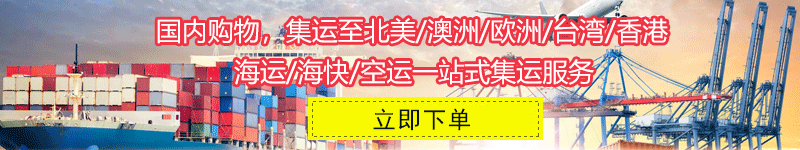大家好,我是霞姐。
在“看见乌坵”系列的上一期,我们讲了水鬼队长吴淼火的传奇经历:
水鬼队长逃离乌坵24年后,他第一次接到高丹华的电话,就关切问起:“你们的小学老师他还好吗?”
这个一直留在水鬼队长记忆中的小学老师,叫蔡玉尖,他和乌坵岛的情感,更加深切,也更加复杂。
台湾核废料存放事件爆发后,蔡老师跟我回了乌坵一趟。
他当时已经是癌症晚期,是杵着拐杖回的,那也是他最后一次回自己深爱的家乡。
从乌坵回来后,他知道时日无多,开始整理手中那些珍贵的老照片,并一一交给我。
蔡老师虽然没有明说,但我知道,他希望我能继续呼吁保护乌坵岛。
蔡老师是第一个积极鼓励乌坵孩子离乡念书的人,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后来的我。
他对我的教导与期望,不亚于我的父亲。
蔡老师叫蔡玉尖,说到他,先要说一下乌坵的教育。
乌坵身为台湾最后一个军管岛屿,地属离岛的附岛,这也让乌坵有其在先天历史与地理的宿命。
虽然台湾当局在行政上拥有乌坵,但实务上常常将乌坵遗忘,比如教育。
乌坵国小最早的前身,是1950年左右,由军统戴笠手下的子弟兵傅培琦所创建,他堪称乌坵最早的阿兵哥老师。他的故事,我们后面再讲。
我妈妈和蔡玉尖都是这个傅老师的学生。在妈妈的记忆中,她和玉尖、元珍、秋菊、凤英都是一块儿上学的好伙伴。
灯塔可以是他们的教室,妈祖庙、破屋内,也照样是他们求学问的好场所。
蔡玉尖的祖父蔡能就是我的亲外公,所以,蔡玉尖其实是我的亲表哥,但他和我妈妈只相差3岁。
因为年岁相仿,俩人不只是姑侄,从小就是念书上学的好伙伴,更是彼此相依为命的精神依靠。
但这对姑侄很苦命。为什么苦呢,我的妈妈生于1944年,4岁丧母;表哥生于1947年,也是4岁丧母。
据我妈妈回忆,表哥母亲病重时,侍母至孝的表哥,路都走不稳,就会拿了杯子到邻居家去要开水,回家给妈妈喝。
姑侄从小失去母爱,每当听到“世上只有妈妈好……”妈妈晚年形容,那真是心如针刺。
后来家里还发生了一件事,差点要了表哥的命。
乌坵岛上的生活很苦,喝水很困难。全村人就靠那么一口井过活,但井水有限,而水对人来说却又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物资。
于是村内就排定挑水轮班表,家家户户都得按事先排定的时间前去井边挑水,万一家里排到的时间刚好是半夜,那当然也只好牺牲睡眠,领略呼啸的北风,在寂静无人的黑夜,勇敢挑水去。
井是深的,水是少的,妈妈和表哥很小就必须分担挑水的重责大任。姑侄分工明确,表哥爬至井底舀水,我妈妈则负责站在井边,利用绳子将水瓢内的水向上拉起。
有回舀水任务完成,表哥由井底的楼梯认真往上爬,眼看就要顺利的爬出井口来了,怎知井口第二阶的楼梯应声断裂,表哥连人带梯就这么摔了下去。
表哥重重的跌入水中,妈妈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见表哥过了许久才浮起,而且还是面朝下,妈妈吓得大哭。
惊慌失措中,见路旁有位阿兵哥在整理菜园,连忙呼叫:“阿兵哥!救命啊!有小孩掉到水里去了!”
所幸有这位好心的阿兵哥协助,才迅速将表哥救起,但不论怎么呼喊,表哥都没有反应。
在寂凉的乌坵,大家啥法子也没有,一家人只能静静的守在表哥的病塌旁,除了心乱如麻求菩萨、妈祖婆来保佑,完全束手无策。
好在几天后,表哥奇迹般自然甦醒,都说表哥是福大命大。
在外公家,我妈妈是女孩,要洗衣煮饭操持家务,希望自然落在表哥蔡玉尖的身上。
表哥自知家境困苦,知道自己是全家寄托,非常努力,专研各类学问。
他人聪明,功课自是不在话下,每当营区有劳军活动,他和伙伴们就是基本演员,节奏感优异的表哥总是担任指挥,带领大伙将快乐带给辛苦的营区弟兄们。
这些大陆彼岸逃过来的阿兵哥很喜欢表哥,教给他许多生活上的技能。
开始岛上的那批国军文化都不低,国学底子很好的,他们看表哥这个小男孩很聪明,觉得以后不能读书很可惜,就要他看报纸。
表哥听闻了他们在外面的见闻,也对海岛以外世界充满了向往。看报纸时,得知台湾另外一座军事管制的岛屿,上面的孩子是可以念书的。
表哥决定也要出去念书,他写了一封信给蒋经国,获得了台湾高层关注,从此开启了乌坵孩子出去念书的大门。
作为乌坵第一个出去念书的人,教育厅把表哥分发在台中一中就读,那是台湾中部男生最好的学校,表哥完全跟得上。
在台中的初期,表哥住在他的大姑妈家,大姑丈就是当年教他读书的傅老师。
在台中的星期假日,表哥则会跟着大家去台中会幕堂做礼拜。由于表哥彬彬有礼,态度谦和,每一位教友都称赞他,在这里他认识了安俐一家。
安俐的父亲在日据时代,曾到东北行医多年,对背井离乡的感受很深,就告诫家人,一定要善待“出外人”,所以他们一家人都很爱护表哥。
安俐的母亲曾感慨说:“在乌坵这样穷乡僻壤,居然也有这么优秀的青年。”
表哥的祖父蔡能,早年跟随英国人学习管理灯塔的知识技能、社交礼仪,以及数十年看守灯塔,对海潮、天体与天气变化的认识,或多或少都熏陶着表哥。
当时安俐才念初二,对妈妈的话毫不在意,只觉得这个青年亲和纯正,没想到俩人后来会结成夫妻。
家贫如洗也让在外求学的表哥尝尽酸甜苦辣,有次暑假回乡,他艰涩跟我妈启齿:“微薄的零用钱早已用完了,一连两天只能喝白开水充飢……”
我妈妈听了既不忍又心痛,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努力帮阿兵哥洗衣服,一件衣服一块钱、一床棉被五块钱,只盼望能多挣一点零用钱给侄子零用。
我妈成家后,甚至连仅有的嫁妆金链也偷偷塞给表哥,希望可以尽点微薄之力。
这种除了血缘之外的患难真情,让我们两家人联系得更加紧密了。
表哥台中一中毕业后,本可以选择更好的大学,但他立志回金门中学念特师科。
因为这里只需密集培训一年后就可毕业,就能回乌坵任教了。台湾虽然进步繁荣,但乌坵仍旧是他的最爱,见过外面世界的表哥知道,要改善故乡唯有教育一途。
在很长一段时间,外地的老师不愿离乡背井来到乌坵,所以就只好从部队中把有学历的阿兵哥抓来充当老师。
这些阿兵哥虽然教的乱无章法,但从协助一群小毛头认识文字,改变孩子们一生的角度看来,如此的“战功彪炳”,实在可说是乌坵的战地英雄啊。
1970年,表哥回到乌坵,也成了乌坵第一位土生土长的老师。
自是从表哥开始在乌坵任教后,我就不曾再称呼他表哥了,不论私下还是公开,我都叫他蔡老师。
那是一个学生,对师者发自肺腑的尊敬。
蔡老师上课的时候太严格,比阿兵哥严格太多太多。
我记得很清楚,默写忘了一个字或者错了一个字,是要打几下的,我们好几个孩子常常手是肿的,就是被蔡老师打。
可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恨他。年纪越大越感谢他,如果没有他这样鞭策我们,我们根本不晓得怎么读书,也根本不会想要去读书。
蔡老师上课很严格,但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还教我们唱歌,我记得有一首歌叫《再试一下》,歌词有一句是:“这是一句好话,‘再试一下’……”
就是鼓励我们遇到困难,不要退缩,要再试一次。这句话对我往后人生,帮助很大。
岛上物资很匮乏,我们没有美术劳作的材料,蔡老师想方设法解决,就有了一个巧思。
那时台湾发起学生给前线三军将士写信,很多学校会寄卡片给乌坵的军人,阿兵哥收到卡片看完后,有的就扔掉,有的就会送给我们。
蔡老师就教我们把卡片写字的地方,慢慢用手在顶尖的那个地方撕开,撕开之后下面那一层我们再把它贴上白纸,就变成的新卡片。新卡片再寄到台湾去,用这样的方式和岛外的学生交流。
蔡老师第一个鼓励大家都出去读书,而不是守着乌坵。在蔡老师的努力之下,很多青少年男女都来台湾升学,有不少都完成大学教育。
也从他那时才开始,我们才开始只要小学一毕业就整批出来念书,女生也才有机会走出乌坵岛。
可以说,要不是蔡老师,根本就没有后来的我。
这个时期,和蔡老师搭档的阿兵哥老师叫骆宗华。
骆宗华的父母都是随着兵工厂从山东青岛撤退到台,他们一家四口就住在台北现在很有名却拆掉的眷村四四南村。
他从凤山陆军军官学校退学不到一个月,根本没时间准备台湾的大专联考,就接到“兵单”入了伍,一个月后就被送到外岛中的外岛——乌坵的大坵屿当大头兵。
知道分发到乌坵当兵时,骆宗华心中充满问号,乌坵?那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它的位置在哪里?离台湾有多远?打开地图怎么找也找不到乌坵这个地方。
心里又想,不知道在乌坵苦不苦?那里会不会有危险?要是共军打过来怎么办?就这样怀着忐忑的心情,在高雄等了一个月,才坐上“中”字号运补船。
一般新兵菜鸟都被安排在下舱,船摇晃得很厉害,呕吐声此起彼落,天黑了又亮,已经超过二十四小时了,怎么还不到?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团疑问。
这时大家都已经吐翻了,也臭昏了,后来才知道原来船在澎湖外海等潮水,原本只要二十多小时可到的行程,这一趟却花了三十六小时才登陆乌坵。
乌坵属于金门县,地理位置却在新竹和台中之间,对面是中共的南日岛。
当“中”字号运补船到达乌坵时,中共做工事的爆破声及火光,骆宗华都听得、看得一清二楚,心里只是念着:妈祖呀,请多多保佑啊。
他在回忆中说道:“至于当时是怎么从‘中’字号船上到乌坵工兵分队的都不知道,只记得在紧张、恐惧中,无意识地跟着口令、人群移 。”
驻军指挥部严格规定所有军人未经报备、核准,谁都不能擅自进入乌坵百姓居住的村落内,违反规定者,一定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为了防范共军登岛,大坵屿全岛到处布满胶雷(人员杀伤雷)。
除了用推土机推出的小泥巴路外,谁也不敢到处乱走,加上管制严格,各分队、据点、哨所平常各自执行勤务,根本老死不相往来,谁也不认识谁。
台湾对乌坵的补给,每三十天一次,主、副食品、油料、淡水、蔬菜,连与台湾的书信联络,全靠海军“中”字号舰定期运补与传送。
运补船一到,除了卫哨勤务人员,全岛官兵总动员卸载,大家这才有难得一见的机会。
官兵到了乌坵,除了返台洽公、调职和退伍,只有“在岛休假”,没人能够离开乌坵返台休假。
幅员不大的乌坵屿,“在岛休假”除了到福利站走走、买买日用品,只能在自己分队的势力范围内闲逛、看海。
又因为保密防谍管制严格,看海看太久,也会被怀疑可能有不当企图,官兵唯一的“正当”消遣,就是到中正堂去阅读过期的书报杂志。
骆宗华有机会和乌坵百姓接触,是从当阿兵哥老师开始。
骆宗华刚到乌坵没几天,有一天,从指挥部回到分队的红标士官长劈头就问他到底犯了什么错?为什么政战主任指名约见他?
骆宗华丈二金刚摸不着头绪,紧张地连回不知道,匆匆忙忙跑向位于灯塔附近的指挥部报到。
政战主任见了他,只简单地告诉他到乡公所找乡长兼大坵国小校长杨瑞大报到,骆宗华领了令,也开启了他乌坵“阿兵哥老师”的服役生涯。
杨校长是乡长兼校长,是个老救国军,声音洪亮,一副军人做派。
当年因为岛上取水困难,常要到两三里之外的工兵分队去取水,在骆宗华的印象中,杨校长经常是挑着两桶水,悠闲地漫步在岛上。
乌坵岛上大、小坵屿各有一间国小,大坵国小一至六年级各有七、八个学童,分成一二年级、三四年级、五六年级三组上课。
一二年级由蔡玉尖,三四年级骆宗华,五六年级黄姓海军联络官担任老师,大家共在三间教室上课,上午一个年级,下午一个年级,没有受课的学生则自修。
教师手册、学生课本都由县政府配送,课外补充教材、月考试卷则由老师自己用复写纸手写制作。
月考对乌坵的老师来说可真是一件苦差事,为甚么呢?因为每个老师教两个年级,每一个年级有五到六科,那时学校连油印都没有,一切都靠复写纸。
每一个年级大概有六至八人,所以一张考卷要复写两次到三次,那时便完全靠老师手写的功力,一段时间下来,大家的手指都长茧了。
学校虽又远又小,但教育命令无远弗届。当红叶少棒风靡全台湾岛时,教育部通令全国培训少棒选手,各地无不纷纷成立少棒队,乌坵自不例外。
大坵国小也接收了完整成套的棒球用具,可是当所有的装备都到齐后,才发现乌坵根本无法成立少棒队。
原因有两个,一个原因是没有训练场地,乌坵都是高地,球一打出去便入海了,另一个原因是乌坵根本没有足够的男丁,根本难以组队,球具只好塞到床底下闲置。
在他的记忆里,当老师没有处罚、也没打过学生,逢年过节时,还把部队准备应节的糖果、饼干作为奖励学生的奖品。
骆宗华的大兵月俸280元,阿兵哥老师的津贴却有400元,在无处消费的乌坵,他从没领过军饷,全数存入同袍储蓄会,这笔钱后来因陆战队接防乌坵不知去向。
因为任教,又因为年龄相仿,骆宗华与蔡玉尖老师很快成了好友。在骆宗华看来,蔡玉尖是乌坵少有的青年才俊,留在乌坵实在可惜了。
骆宗华眼中的蔡玉尖,是个心思很细腻的人,可能因为没有母亲的照顾,所以很多男人不会做的事,蔡玉尖都能先想到、做好。
但他似乎也总是忧心忡忡,有心事的样子。
俩人熟了以后,骆宗华终于知道了蔡老师皮箱里的大秘密,原来里面珍藏着他女朋友的照片。
有一天,不知是蔡老师心情不好多喝了一点酒,还是和他父亲吵架,就把一肚子苦水全吐了出来,骆宗华才知道在台湾有个红粉知己在等他。
一方面他想服务乌坵的教育,一方面又是两人坚贞的爱情,两相比较难以抉择。
而且更主要蔡老师自尊心又强,女友家家世很好,自己从小没了母亲,父亲又只会天天喝酒,根本上不了台面,他要怎么面对这段感情,内心很痛苦。
年轻的骆宗华看着蔡老师痛苦的样子,也只能傻看着那张泛黄的照片,不断安慰他。
此后,骆宗华常以《圣经》所载基督徒受磨难、困境时,如何祈祷创造奇迹开导蔡老师。还给他送了一本《万年长青》共勉。
甚至他还和海、空军联络官一起组成“乌坵开讲”,常在蔡玉尖老师房间的床板上天南地北高谈阔论。
骆宗华温暖的友情,稳定了蔡玉尖的情绪。
为了鼓励大自己两三岁的蔡玉尖继续进修,骆宗华当时也准备考大学,他不但提供考大学的相关资料,还利用学生自修时间俩人一起研究新数学、物理学科。
因蔡玉尖的父亲是灯塔管理员,骆宗华得以多次上到乌坵灯塔。灯塔在指挥部全岛的最高点,进去后才发现,虽然灯已经不发光了,但灯塔里面真是洁亮无比。
特别是灯上的反射棱镜更是擦得一尘不染,这让骆宗华对灯塔的两个管理员大为吃惊,真切体会到什么叫尽职尽责。
这两个管理员,一个是学生高丹华的爸爸高金振,另外一个就是蔡玉尖老师的父亲蔡云清。
两人不仅把灯塔管理的干干净净,据说民国五十几年时,有一次为了保护灯塔的油料不被贪污,俩人得罪军方,反遭军事软禁一周,并罚每天挑水。
这种对工作的尽心尽力,让年轻的骆宗华刮目相看起来,也对乌坵有了不一样的看法。
骆宗华知道自己快离开乌坵时,还特别去了一次灯塔,在内墙壁上涂鸦“万年长青”四个字。
这是董显光博士所写的一本日记,他是著名的外交家,他每天自我反省写成的这本日记。
骆宗华常在阅读后藉此自我反省并融会贯通,也编一些故事讲给孩子们听,和孩子们一起勉励,对孩子很有激励作用。
当时前线虽然物资乏,但是孩子们求取知识的欲望却很强,骆宗华退伍回到台湾后,又寄了多本给蔡玉尖老师,请他送给孩子们看。
乌坵当时的驻军大多由南海游击队改编,官兵年龄偏长,骆宗华和他们至少有一、二十岁的年龄差距。
身为年轻菜鸟新兵的骆宗华,只能乖乖地跟着老士官长作息,想要平安度过一年十个月的役期。
这些老士官长中,让骆宗华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夏姓老士官,他负责管理操作海水淡化机房。
因为年长,体能老化,为了吃一顿饭,得费力地从海边机房步履蹒跚、费尽全力才能爬上陡坡顾上三餐。
这让骆宗华看了都于心不忍,常常帮夏班长送饭。
飓风来的时候,海水强力拍打机房墙壁,巨大的声响,彷彿随时都会将墙袭垮,骆宗华还冒着风雨去关心夏班长的安危。
这些和骆宗华朝夕相处的老士官们,有人之前是出家门买瓶酱油就被抓了壮丁,之后再也回不了家。
以骆宗华这样一个菜鸟新兵的观察,这群人的心理是随时都可以死,根本就不想活了。
因此,隔着海,他们思乡情切的痛苦严重到想自杀一了百了,这样的情绪,让他们夜夜流泪痛哭,只能用酒精麻痹自己。
好在有乌坵灯塔管理员蔡云清,和老士官们相处融洽,也互动热络,他提供了一间拥有简单炊具的小房间,让老士官们可以自由出入。
思乡心切的老士官们,还能自己开开小灶、打打牙祭、喝喝小酒,暂时消解了一下苦闷的情绪。
士官长老丁就很会做菜,他的拿手绝活是:将蟹壳剥开,倒一点酒,用大蒜、辣椒调味,其味鲜美无比。
他再做上几道菜,便拉着大家一起吃饭,每次都说谁谁谁过生日,大家也就举杯祝他生日快乐。
后来蔡老师告诉骆宗华,每当有渔船回来,老丁拿到鲜货都会到蔡老师家办桌,美其名为过生日,实际上是打牙祭,一解思乡之苦。
由于官兵们不定时来来往往,蔡老师的父亲除了灯塔上工、睡觉,几乎随时接招陪喝两杯,他也由此常常红着脸不退色,因此被官兵们戏称为“关公”。
红脸“关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排解自己的苦闷,也化解老士官们那些无法自拔的乡愁。
“关公”也有他的苦闷,两岸分治后,他的母亲被留在湄洲岛,未能再见,中年又失去爱妻。
他生于这座孤岛,内心也是孤独的吧。
1974年,蔡老师考上台湾师范大学生物系,重返台湾念大学。
他就读师大二年级,女友安俐已在国中任教,两人开始论及婚嫁。
此时乌坵家贫依旧,我妈妈给新人一枚戒指,以及平常省吃俭用的六万元,只希望侄子可以就此摆脱家庭的阴霾,勇敢的开创属于自己的幸福未来。
蔡老师成家后,对我们一家一如既往地好。对我更是如此,既是妹妹,又是学生。
我在台中女中上学时,患上肾脏炎必须休学,也是蔡老师把我接到他们家休养,他和表嫂更是尽心的照顾我。
当时我怎么医都医不好,蔡老师在师大生物系学生物,有一天他就把我带去给他的教授,他的教授会点中医。
教授看完就告诉他说,我需要吃什么什么药,我也听不懂,只知道哪个市区买不到。
所以,表哥就要跑到山上去找那个草药,打成汁水给我喝,我妈妈从乌坵来照顾我的时候,也是他去摘草药。
记得我第一次离开乌坵,也是表哥带我出来。
我小时候天天陪在外公身边,外公因肺病去世后,家里担心我也染上,就让蔡老师带我上台湾检查。
那时候蔡老师正在经历艰难的异地恋,他到了台北很想能单独见一下女友,带我检查完后把我安顿在亲戚家里,说他有事要外出。
我那时太小,根本不懂,死活要跟蔡老师一起去,蔡老师竟然也没有凶我,又因为我晕车厉害,他还细心准备好好塑料袋,就带我一起去见女友了。
两个难得一见的情侣,根本没有机会牵手,只能牵着我这个大电灯泡去逛公园。现在想想很好笑,但也可见蔡老师是多么善解人意的一个人。
后来,我妈妈也带着弟弟妹妹出来读书,租住在彰化一个很简陋的房子,蔡老师知道后,就和我妈妈说,他台北岳父家还有一户房子空着,可以来住不用给钱。
我妈妈欣然前往,去住下才知道,原来是蔡老师夫妇私底下悄悄付了房租。妈妈得知后肯定不愿意拖累侄子,她一咬牙东拼西凑借了点钱,买了我们家在台北的第一个小房子。
这种血浓于水,相互体谅的亲情,是很珍贵的。
在这期间,蔡老师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
我们高家和蔡家,是乌坵岛上最早的灯塔守。我的曾祖父蔡土球与外曾祖父高珍原本是亲手足,其中一人由对方家庭收养,成了异姓兄弟。
1872年,大清海关规划兴建灯塔,兄弟俩双双从湄洲岛到乌坵参与灯塔兴建。
塔完工后,蔡土球和高珍兄弟俩定居下来,成为乌坵灯塔第一批看守伕,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灯塔守。
1949年之后,看守乌坵灯塔者有蔡家两户,加上高家、吴家共四家。其中,蔡能和高瑞翁除了是两代近亲之外,更是儿女亲家。
蔡家分良知,蔡荣与蔡能。蔡荣1950年4月调往南澎灯塔途中失踪,这个家族除了看守灯塔,成员先后担任乌坵的乡长或乡代表,一直稳坐至今。
而蔡能这支血脉本来拥有岛上最多土地,但因为人丁单薄三代单传而遭受欺凌。他与高瑞翁二人不仅继续父业守护灯塔,还结成儿女亲家。
两人退休后,两人的儿子蔡云清、高金振子承父业,就是我的舅舅和父亲。
蔡、高两大家族堪称“百年灯塔家族”。本来是岛上人口最多的两户人。可因 1949 两岸不能往来,好多亲人都分隔在湄洲岛,我们从人数最多,变成人数最少。
乌坵是到1954年起才开始真正设户籍。设户籍的时候,我们大坵村总共只有七户人家。从乡公所那边开始编号码,舅舅家正好是7号。
其实他们家是最挨近灯塔的,如果从灯塔数的话,应该是第一号。
到七十年代的时候,乌坵岛上有些老房子开始漏水,舅舅家是岛上最早的人家,所以他家漏水漏得最严重。
这个时候军方就说大坵民众很穷困,住的很不好,所以军方帮盖房子分配给你们。结果,就把他们原先一栋最好的房子给拆掉了。
熬了一年多,1976年8月忠义楼终于完工,舅舅心想可以分到一间房吧。没想到公家却硬不配给,不过是扔下一句:“你一个人要房子做什么?”
舅舅心有不平:“什么一个人,我还有儿媳妇在台湾啊!当初盖房子时,我已表明也要有一间啊!”
只见公家又说:“一个人不够分到忠义楼,要两个人以上才能分得到,你叫他们把户口迁回来,我就给你一间。”
明明是自家的房子,明明是被强迫拆除,明明是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丝的赔偿,如今却换得想要分间房子都是痴心妄想。
舅舅只好将儿子媳妇的户口统统都给迁了回来,没想到,到头来还是一无所获。就此委身在破旧的老房子。
老房子屋顶像龟壳般,每到下雨房子就像米筛子般落不停,每到下雨老人家就越是心烦越是自暴自弃,自此他更加日夜藉酒消愁以解郁闷。
他喃喃不解:“为什么拆我的房子却连间房子也不愿给我?!”
无数的为什么,像着酒精般塞满了老人家的所有思想与血液,酒,终于将老人家带走了,他,就这么离开了。
他曾经说过:“我死也要死在忠义楼!”他真的这么做了。
舅舅真的死不瞑目,好多村民和我讲,夜里他在忠义楼的屋顶走动,喊话,并且滚小石头,把全村的村民吓得魂飞魄散。
蔡老师只希望通过努力,可以给爸爸过点好日子,没想到为了间房子父亲早早离世。
蔡老师了解父亲可怜,也明白父亲不过就是图个避风遮雨,却连这小小的念头都无法如愿,孝顺的蔡老师又岂能舍得?
据表嫂回忆,蔡老师表面乐观欣喜,但年幼丧母,中年丧父,心中总有内疚之感,有一天,表嫂见他伸手一抓,一撮黑发便随手落下, 这是心力交瘁的结果。
蔡老师台湾师大毕业后,就赴金门烈屿国中任教。据金门文史工作者林马腾回忆,他在金门国中和蔡老师有过共事,每次说起蔡玉尖都是肃然起敬。
在他的记忆中,蔡老师是非常认真的老师,常利用周六、日自己加班制作标本,又设黑白照片冲洗室,非常忙碌。
现在看那些标本不算什么,但七十年代,蔡老师就做了生物教室,自己做很多的标本,野鸭、鸟、鱼各种动物标本,泡在福尔马林里。
现在回忆,林老师还感叹说后来蔡老师全身都是病,是不是和那些有毒标本有关。
不仅如此,当时金门军事管制区照相也是被限制的,蔡老师就自己做了个暗房,自己冲洗照片,现在很多老照片,都是蔡老师留下来的。
还有一次学校月考,当天晚上印考卷的机器坏了,第二天的考卷印不出来,大家都说完蛋,明天月考没考卷了。
蔡老师二话不说,检查了机器发现坏了一个零件,当时也没地方买新零件。蔡老师就连夜去东林铁工厂买一块铁片,一直磨到天亮,竟把这个零件给磨出来了。
蔡老师是学生物,跟机械完全是两回事,大家都想不出他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只觉得他是在变魔术。
但我相信,只有蔡老师才做得出来,他不仅非常的有才华,还非常的有毅力。
四年后,蔡老师从金门调回台湾。
1983年任教国立华侨中学,历任设备、研发、训育、教学组长及教务主任。
直到1994年,他才因病才辞去教务主任职务,他来去外岛共十三年,那算是漂泊孤寂的岁月,在侨中这十年,是他生命中璀璨安定的时光。
最后几年都在生病中,他坚强刚毅,只要体力稍稍恢复,都会销假上课,从不沮丧、畏惧。
这期间,蔡老师一直想将户籍迁回乌坵,落叶归根,乌坵才是他的家。
很可惜,由于乌坵的军事管制造成的行政颟顸,县政府户政单位说他家是空户不能迁。
再后来,蔡老师家的七号门牌却被偷偷移给因核废料而迁籍的外来人,大坵村最早的这一户就变成没门牌的黑户。
蔡老师思乡心切,在住院、在化疗的多承重压力下,又从抵押借贷的医药费里硬是拿出了几万块钱,拜托亲友协助将乌坵岛破旧的老屋翻盖。
他说:“这样才对得起父亲!也是我最后的心愿。”
后来,在李毅强乡长与指挥官的协助下,房子是已盖了,不过也只盖了一层,因为再也没钱可盖了。
1998年,台电拟在乌坵储存核废料,蔡老师得知后立刻联络连络乡亲,表达意见。
其实他不反对政策措施,他学的是生化,关于核废料对地球生态影响有明确认知,就不能不表达看法,也帮乡亲们分析分析。
蔡老师化疗刚告一段落,他不愿坐视原乡遭受污染危害,拄着拐杖,让我带他岛台中港搭船前往乌坵。
回到家乡,他拖着病体,去倡导核废料对海域生态的危害性。核废料一事尚在评估中,未来发展如何是国家的事,他已尽了心力。
1999年2月4日11时24分,蔡老师卸下世上的劳苦,离开人生。
蔡老师是爱乌坵的,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恳求我们将他的骨灰撒向家乡的大海。
他想和爸爸妈妈在一起,他想和祖先穷尽一身死守的乌坵灯塔在一起,他想和孕育他成长茁壮的乌坵碧海蓝天一直生生不息。
但我们做不到,因为舍不得。
我后来一直在为守护乌坵而奔走呼吁,很大原因是受蔡老师长期的影响,骨子里我觉得我所做的一切也是他想做的。
回望这一路,时间过得真的很快,有高潮,也是低潮,我们都是时间的过来人。
我现在已经活过超过蔡老师在世的年岁,我也平和了很多。每次遇到困难时,我就会想起他曾经教过我们的歌《再试一下》:
“这是一句好话,‘再试一下’……”
我重返乌坵岛时,就在蔡老师家的门口画上十字架,我就希望岛上的人记得有这么一个人。
他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为乌坵开出一条教育之路。
也希望岛外的人看见乌坵灯塔时,也能看见乌坵岛上这样一个有为青年。
从聊天中,能感受到高丹华对蔡老师的深情。
那种深情并不激烈,甚至有些平淡无味。我希望她能还原更多的细节,但她却常常记不起来了。
我很理解这种情感,很像我们要讲身边最亲近的人时,往往不知从何讲起。
但她给我找来了很多人对蔡老师的回忆,母亲的、表嫂的、阿兵哥的,以及蔡老师的同伴,这些回忆有长有短,但我知道高丹华在背后所做的努力。
她想从别人的回忆中去拼凑出完整的蔡老师,以此来完成对蔡老师的致敬。
我问她,为什么那么想记录蔡老师的故事。
她说,台湾军方和县政府欠蔡老师一个道歉。
他们家作为百年灯塔家族的后人,在乌坵岛上是第一户建盖房屋的,但老屋拆除盖了新房后,他们家没有分到新房更没获得补偿。
而蔡老师更是,先不说他对乌坵教育的贡献,不仅属于他家的7号没了,他还成了乌坵的黑户。
唯有记录,方能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