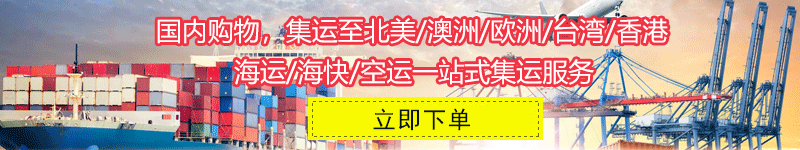点击蓝字
关注我们
我自来对中文都非常喜爱,并打定主意要到大学攻读中文。高中毕业之后,我有幸为台湾大学中文系录取。1964年9月,我兴奋异常地整装前往洋溢着秋的气息之台北升学。
大一印象最深刻的课是叶庆炳老师教导的大一国文(课本是《史记》和《左传》)。叶老师讲解课文深入浅出,生动有趣,极具启发性,我受益匪浅,还曾和同系的学长提起自己上叶庆炳老师的课之感受。学长却说:“你还没上过另一位叶老师的课呢。明年上‘诗选’时,你会更加的惊叹。”学长指的就是叶嘉莹老师。
升上大二,“诗选”一课果由叶嘉莹老师负责教导。老师气质高雅,教学不落俗套,谈吐缓急适中,学富五车,记忆力超强,上课时引经据典,左右逢源,拿捏得妙,对中国经典,倒背如流,诵诗如行云,解诗如流水,轻松愉快,游刃有余,把中国诗歌的美学发挥得淋漓尽致,堂堂精彩,令我们对她所赏析的诗歌总是心有戚戚。老师授课那种一气呵成的流动之势,成了学府里独具风采的传道景观,课堂上的典范,令听讲者佩服得五体投地。
被老师的教学魅力所吸引的不止是中文系的同学,许多外系的学生也依时到来旁听,因此弄到我们常常找不到位子坐。迟到的甚至要在科室外站着听课。最近读到比我早两届的台大外文系学长淡莹(刘宝珍)在《南洋商报·南洋文艺》版(2014年元月21日)发表的散文〈让种子萌芽的土壤〉,忆述她当年如何到中文系旁听“诗选”一课。文章颇能反映叶老师授课的情景,故特迻录于下:
在台大中文系修读四年,收获良多,尤其是叶老师所教导的诗歌赏析之法,
更使我对教中文深具信心。大学毕业之后,我回到马来西亚,便毫不犹豫地选择到中学去教中文。返马不久,我就应聘到东马沙巴州保佛中学任教,主要乃是教导我所喜欢的中文课,我于是满腔欢喜地走马上任。事隔没多久,因校长另谋高就,学校董事要我接任校长之职。当上校长之后,由于行政工作十分繁琐,常恐从此无法专心读书和从事研究工作,于是顿生离职再度出国深造之念。
沙巴地处边远,较少机会与外界联系。我还在台大读书时,叶老师已远赴美国讲学。因此,那时我以为叶老师仍在美国。正当我打算再度升学之际,有一天翻阅加拿大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刊,发现原来叶老师已在那所大学任教。心想,若有机会再逢难遇的师表,继续向老师学习,该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我一时兴奋莫名,立即向该大学申请入学,同时也将此事上报叶老师。不久之后即收到老师温馨的回函,并说会尽力协助我到那里深造,令我喜出望外。有老师的协助,我的申请果真十分顺利。接到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入学通知之后,我便辞去保佛中学校长之职,带着内人,远赴加拿大升学。抵达温哥华时,正值秋高气爽的九月中旬。
老师当年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系硕士班所开的课为中国文学专题,内容主要是诗、词、曲,也包括一些古典文论,是两学年的课程。老师讲课一如往昔那样天马行空,仍旧精彩绝伦;不过却多了一些讨论的时间。我从这个课程得益最多,所写的诗、词习作也承蒙老师赞扬和鼓励。
当时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系的系主任是蒲立本(Edwin George Pullyblank)教授。我上过他所教的“中文研究法”和“中国声韵学”两门课。只因我在台大时修过许世瑛老师的“声韵学”,所以应付蒲老师“中国声韵学”这门课还算得心应手,讨论问题时也往往能切中肯綮。他又知道我的籍贯是福建安溪,有一次在“中国声韵学”的课堂上,他问起我想不想把硕士论文定在闽南方言研究,并且说如果我作这样的选择,他可以当我的论文指导老师。我因为一心只想向叶老师多学些中国古典诗歌方面的学问,所以蒲老师好意要我研究的课题我就没有应承下来。最终我决定以“韦应物的生平及其作品重评”作为我的硕士论文题目。叶老师也答应当我的论文指导老师。
在温哥华老师和师丈生活虽然忙碌,有时还腾出时间请我和内人到老师府上吃饭和吃饺子。小女韵璇出世时,老师还特地赠送一块非常精美的银盾给她。对老师的细心关照,我们一家人都非常感动。小女至今还将该银盾视为最难得的珍藏。
我的论文答辩于满地覆盖着厚雪的1975年杪通过。事前本来曾向老师提起毕业后拟到气候温和,四季如春的夏威夷深造。老师还说他的高足罗锦堂教授正在夏威夷大学任教,若我果真想取得在美国大学作研究的经验,老师可以特别向其高足举荐,如此之下,应该不会有大问题。进行申请之前,家父不幸遽然逝世,因此我取消到美国升学的念头,于翌年带着家眷返回马来西亚。
抵马后,我先在雪兰莪州巴生光华独立中学当校长,后来转至玛拉工艺学院(今已升格为玛拉工艺大学)任教。自己觉得此两处都无法发挥所学,于是1980年又转到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在这里不但可以教导自己喜欢的中国文学,而且还有专心读书和做研究的好环境,与学生又互动频仍,教起书来也相当顺心,喜悦之情,自不待言。初到马大中文系之日,令我感到高兴的另一件事就是竟然得到几位曾受叶老师亲炙的同事之称许,说我已颇得一些叶老师的真传。马大当局还特别礼邀叶老师出任中文系的校外考委。在叶老师之前担任马大中文系校外考委的教授依序为李田意、柳存仁、饶宗颐、屈万里及施友忠五位,叶老师是第六任。按马大惯例,校外考委一任三年(叶老师的任期从1980年至1983年),任期内可到马大访问一次,为期一周。当时老师因为讲学与研究工作过于忙碌,所以无暇到马来西亚一游。
1993年,马大中文系非常隆重地邀请世界各地著名学者参加“国际汉学研讨会,以庆祝创系30周年纪念,叶老师当然也在受邀者的名单里。其他学者包括中国大陆的冯其庸、金启华、刘梦溪、谭家健,中国台湾的王叔岷(王老师虽寄来论文,却因事未赴会)、苏莹辉,中国香港的金耀基、赵令扬、邓仕樑、郑良树,澳洲的柳存仁、何炳郁(时任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主任)、颜清湟,德国的傅吾康(Wolfgang Franke)新加坡的陈荣照、何启良等教授。
叶老师在研讨会上所展现的风范,令出席者和学生们都钦佩不已;加上老师的盛名,许多机构这时都乘机争相邀请老师到各地去讲演。第一场在吉隆坡(《星洲日报》主办),第二场在北马槟城(《星洲日报》与《光明日报》联办),第三场在南马柔佛(南方学院主办),第四场在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主办)。如此不当的安排,弄到研讨会过后那几天,老师几乎日日都要辛苦奔波和讲演。我们至为懊恼,内心也一直感到愧疚当日没有及时阻止一些机构的邀请,遂使老师因此而疲惫不堪。
当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的系主任,正是我一向也极为敬慕的业师陈荣照教授。乘叶老师当日南来之便,陈老师即请叶老师于翌年到新大当客座教授。叶老师在新大时,我曾与朋友赴新拜谒。记得老师当时还提起新大原本的聘约为期一年,可是由于不习惯新大朝九晚五的刻板上班制,老师只答应逗留一个学期。新大中文系的学生想必为此而叹惋。
我非常幸运有机会在中国台湾、加拿大、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敬仰叶嘉莹老师的风范。老师桃李满天下,不论在杏坛或学术界,都有异常丰硕的收获,卓越的成就。今年适值老师九十华诞,我又多了一个在中国天津敬仰老师风范的机遇,并祝愿老师身体常健,生活平安快乐,万寿无疆!
审校:张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