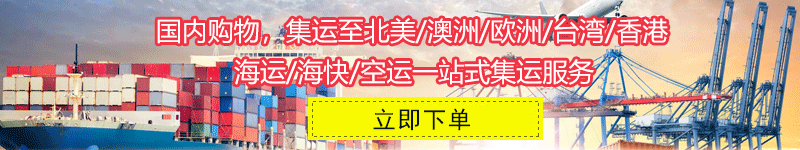原创 帆子 三明治
文 | 帆子编辑 | 依蔓
2020年2月7号晚上,加拿大多伦多国际机场人来人往,看不出疫情即将在这个城市爆发的迹象。经过了15小时的不停顿飞行,换了5个医用口罩后,我背着大包小包下飞机,向入境处走去。这是中国南航从广州飞多伦多的末班航班之一。一个星期后,航班停了,重开遥遥无期。
就这样回来了。15个小时前我还在和父母亲人拥抱告别。一万多公里的空中飞行距离,隔开了两个相差12小时的时区,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人群和气候。几乎每一年,我像一只候鸟一样飞回南中国,和家人朋友匆匆相聚两周后回来,每一次情绪总会波动一阵子,思考一下“我从哪里来”之类的宏大命题。这次也不例外,疫情让心情更复杂。
在入境海关柜台前,穿着制服的棕色皮肤小伙子完全不知道我的内心躁动。他让我摘下口罩,看我一眼,盖个戳,然后说,“Welcome home (欢迎回家)“。他的脸平淡如“扑克牌”,我没好意思告诉他,这句例行公事的问候,让我安静下来。是的,这里也是我的家。
从什么时候开始,异国他乡成了家?一定不是2003年。那一年,我刚刚移民加拿大。
这是一条毫不含糊时间线:收到移民签证并完成体检后:1年内必须登陆;5年内住满2年,可以维持移民身份;5年内住满3年,可以申请入籍。每一个移民加拿大的人,不管他来自何方,背景如何,都需要参考这个五年规划,和千万新移民走上一段重叠的人生轨迹。2003年,我和近3万中国内地移民一起登陆加拿大,开始了这段轨迹。“登陆”,“landing”,这个词透出一股打仗时吹号冲锋的紧迫感,一种要探索新大陆的悲壮感,实际上,许多人的移民之路少了义无反顾的坚定,多了左思右想的权衡,一路走来,拖泥带水,好像是被谁忽着移民似的。
但没谁忽悠我,是自己把自己忽悠出去的。
说起来,都怪一个约过会的男生,他让我看了他的移民申请资料。我一看,不复杂呀,咱也来试试。凭着一流的“抄作业”能力,我的进展出奇顺利,比他还快。递交了申请之后不到一年,在2002年的春天,一个来自加拿大领事馆、装着移民批准文件的大信封飘然而至。记得那一天,回南天的潮湿让人浑身黏糊糊的,文件上红印章却很清晰。我想,难道这下就要出国了?
出国,对我这种生于三线小城、父母不会说英文的孩子来说,有点遥远。按理说在洋气的大上海读了四年大学,周围都是考托福的同学,四年间陆续有人退学奔赴北美名校,多少应该受到熏陶才是。可是在90年代,出国留学这事儿可望而不可及。
2000年,大学毕业后,我到了一个广州民企上班,很快跳到了一个正在急速扩张的知名外企做技术支持工程师,给通信设备排除故障。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就是冉冉升起的华为。那些年正是外企的黄金时代。白领一族穿着笔挺的职业装,拎着黑沉沉的笔记本电脑包,出入星级酒店,意气风发。
当看的资料是英语、写的邮件是英语,名字都变成了“Mary”的时候,我的英语水平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进步,随着在工作中接触了不少外派到中国的欧美同事,外面的人和世界也渐渐真切起来。
那时来中国的老外多数都是总部的技术尖子。我们跟他们学习技术,他们在观察这个陌生的国度,常有惊人之举。有一个荷兰工程师在深圳时不幸“中招”,不知吃了啥腹泻不停,一路长途飞回去,苦不堪言。后来再不来了,顶替他的同事呆了两周,硬是没有吃任何餐馆的热食,全靠自带干粮续命。我们把他拉进海鲜豪华酒家,芝士焗大龙虾点上了,对方就是不举筷子,笑容很得体温和。
他们对中国了解,往往限于出发前在公司上的中国文化课,讲的都是什么中国人打功夫,爱喝茶和搓麻将之类的东西,让人哭笑不得。中国人不也是对外国有很多假设吗?比如,我以为他们跟我一样,每天不喝开水就不行。第一次出差到欧美住酒店,没拖鞋,没热水就把我折腾坏了。
那时国家刚刚开放,互联网正在兴起,上网没有高速,进口大片一年就几部,1999年引入的《星球大战》其实评分不高,却足以让国内观众大为惊艳。我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心不可抑制,出国逛逛并非悬念,而是什么时候去、怎么去的问题;但是没有想过移民定居,直到认识的白领们一个个开始了移民的进程。
从1998年开始,中国内地移民总数连续多年居于加拿大总移民数榜首,大约占比15%,成为枫叶之国第五波移民潮中的主流。在那以前,一个普通大陆人居留欧美最常见的途径是考寄考托,留学,毕业后找工作,靠工作签证留下来。加拿大的宽松移民政策,为有学历、有专业技能的白领们提供了“独立技术移民”这一个“低门槛”通道。
得来不难,抉择却不轻松。我像很多拿到了移民批准的人一样,陷入了长考。去,还是不去?
在这长考其间,我结婚了,随即把丈夫周林加到了移民申请里。所以,去不去,怎么去,应该是两个人的决定。然而移民的主导者是我了。他其实从没有移民的打算。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广州人,他在这座城市的根基深厚,日子惬意。广州既有大都市的繁华便利,又有生活之都的悠闲情趣。我有优越的工作和收入,那时互联网正在兴起,欧美电信网络供应商是资本的宠儿,股票涨得令人咋舌,一条条上扬的曲线看不到终点。但没人能预见到,那一波全球互联网经济泡沫很快破裂了,曾经火红的股票都跌成了垃圾股,大批互联网新贵和百年企业齐齐破产,裁员潮一波又一波。2001年,美国911袭击事件爆发,北美经济衰退。同一年,中国加入WTO,经济迅猛发展。
去,意味着连根拔起,漂洋过海;不去,舍得放弃尝试不同生活和深度看世界的机会吗?选择的困难在于我们根本无法准确预见未来,可能怎么选都是错的,既然如此,与其徒劳地努力做到妥帖周全,还不如听从自己的心。
我决定自己一个人先登陆。这种夫妻一人留下,一人出发的模式在当时的移民潮中很常见。分居两地算是中国夫妻的一种传统,不算什么了不得的事。为了想象中更好的生活,夫妻能否朝夕相处并不是做决定的首位因素。上一辈由于各种现实的限制,也是这么过来的。历史几乎是在重演,不同的是这一代人比父辈有更多的选择自由。然而,实用主义终究超越其他一切的标准。
出国后,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谋生。当时的北美经济实在悲观。与其两个人都去,没工作,坐吃山空,不如一个人在国内正常赚钱,一个人到国外打前锋。同时希望“鱼和熊掌”兼得。很多人其实自始自终都没认真想过要去国离乡,但是一时又不舍得放弃发达国家的移民身份,所以先让一个人过去,以后再说。
后来才明白,常常是没有了“以后”。
2003年,北美经济仍处于谷底,科技行业更如同寒冬一样萧瑟。2月份,我在移民身份过期以前辞了职,只身一人来到了多伦多。摸摸兜里的钱,省一点,一两年没问题,既然找工这么难,那我就先不找了。
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大学和研究生招生总是火爆,于是入学申请就是一派“僧多粥少”的景象。凭着优良的教育和工作背景,又愿意付出高昂学费,我最终拿到了多伦多大学理工硕士的通知书。开学后发现,班上大半是“成熟学生”,其实就是对超龄学生的礼貌称呼。其中有被高科技企业辞掉的专才。比如加拿大的“国民之光”北电,就一场场地解雇员工,直到公司解体。想躲避经济下滑期的中国移民也不少。大家在他乡遇到同类人,心照不宣。移民的尴尬和欢喜莫过于此。
班里有几个本地本科刚毕业的同学。跟他们一起做项目的时候,比他们大不了几岁的我,感觉老气横秋。毕竟我经过国内严苛教育的淬炼,在社会上“混”过了,又有漂洋过海的经验,经历催人熟,跟北美蜜罐里泡大的“小鲜肉”不能比,真让人有点怜惜自己啊。
不管什么背景,因为什么原因回炉,这个学是要好好上的。能够在北美一流学府里受教育,暂时躲在书本间,不管外面的风风雨雨,怎么说都是一种幸运。听课,做笔记,搞项目,开会,实习,写论文......全套功夫做足。冬夜里上完课,从校园走回住处,大地被白雪覆盖,空气清冷,天上那一轮他乡明月,皎洁得几乎让人落下泪来。朦胧的眼睛,在看到一盏盏灯光的时候才渐渐清晰。眼前那座14层的楼房,是我在他乡的“家”。
那是多伦多大学的学生公寓楼里,地段一流,闹中取静,离“名店区”和大学校区很近,最大的优点是,租金低廉,所以,申请的人排长队。按学校规定。申请人不能分租,但是因为太受欢迎了,许多人搬进去后就开始偷偷分租,赚点钱补贴租金。虽然我在新移民中经济条件还行,不过在没有工作,没有稳定收入前,是绝不敢大手大脚花钱的,所以要走许多新移民走的路子,那就是合租。
房东是福建人,一家三口,房东一家很和气。男主人不到30的样子,妻子看上去也就二十岁出头,还有一个刚刚学说话的小孩子。夫妇俩都不怎么懂英文,说自己没啥学历,并不是移民主申请人,而是搬进了男方姐姐的住处。看来每个移民背后都有故事。
到了多伦多第三天,我就在这个两居室公寓里的客房里安顿下来。房间设备很简单,一张弹簧单人床,睡上去吱吱作响。一张旧书桌,没有电视机和其他电器。洗手间,厨房和客厅公用。我绝大多数时间都在房间呆着。
每天一大早,妻子出外到工厂打工,冬天的时候也如此,外面还黑漆漆的,大风呼呼地刮。丈夫在家带孩子,脸色常常很沉郁。有几回,孩子哭闹,他哄不住,咆哮起来。“不要哭了!”多年后我当妈带奶娃,才能体会他的无奈和苦闷。或许在国内,他过着一份轻松自在的生活,现在却在一个冰天雪地的陌生国度里,跟一个不能交流的奶娃捆绑在一起。
跟福建一家人住了三个月,我的健康出现了问题。首先是皮肤时不时发红疹子,到处游走。其次,我失眠了。这是头一次长时间失眠,来得莫名其妙。突然有一天就开始了,不是短暂失眠,而是整夜失眠;不是偶尔失眠,而是每天失眠。没有其他身体问题,就是睡不着。只有在困极的情况下,在天蒙蒙亮的时候打个盹,正要入睡时,一个激灵又醒来了。
烦躁,焦虑,生气,完全不明白问题出在哪。是压力吗?我已经决定要在秋天时开始读书,钱还够用,心理上对移民初期的挑战也做了充分准备,自觉压力不大。
很久以后才知道,有些压力,隐蔽到当事人都未必觉察。到一个新地方后所谓“水土不服”的症状,就是压力作用于身体的结果。独自一人来到这个遥远陌生的国度,心理准备得再充分,也有压力。被各种新鲜事物过度刺激,对将来的前途茫茫之感,不稳定的经济,失去了日常和亲友的感情联结,一切一切,都是压力。
可是当时不懂。就觉得住得不舒服,应该换个地方,或许会对失眠有帮助。
为了可以在室内吊儿郎当地穿衣行动,我不想跟男性和夫妇合住了,要找华人女性。照着中文报纸上的“豆腐干”分租广告,我找到了两个女性带一个孩子的两房一厅,在一栋十几层的公寓楼里,地段降了一级,不复原先名店区和大学校区的“高贵”。
开始不明白,这才两个卧室怎么住?一去发现了。原来两个女性是朋友。一个近四十,带着青春期的女儿,一个二十多岁。她们一起住大房,能放下两张床,给我小房间。看着她们房间里一天一地的衣物,我心里叹了口气。好在客厅厨房还宽敞干净,有两个洗手间。这就是多伦多老公寓的好处,空间够。看在低廉的租金份上,又看她俩和和气气的样子,就先搬过来吧。
全女班的住所,如果清洁不太糟,人不太差,多少有种温暖的烟火气。很多女性喜欢聊天八卦,喜欢做饭追剧,即使条件不尽如人意,也会努力保有一点生活情趣。我呆在自己房间里,门开着通风,一边做自己的事情,一边听她们在客厅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尤其在黄昏时分,几乎有种家的温馨气氛。
两个人都没有全职工作。当妈妈的那位打零工。有一天她进了门,大声抱怨,“太脏了,太臭了!”那一天,她在政府为无家可归者建立的收容站清洁卫生,有流浪汉就在床上排泄,难说是故意的,还是喝醉了,或者是健康问题。这些无家可归者,如果外面能混,一般都不愿意进收容所,虽然是免费的。他们大概更喜欢自由。一到夏天,就在街头游荡,反正饿不死。
收容所的环境好不到哪里去,在这样的地方做清洁工,是相当腌臜的工作了,室友但凡有更好的选择,也不会做下去。果然没多久,她去了餐厅打工。
她是怎么来到多伦多的?孩子的父亲在哪里?我没有试图去了解。另一位年轻一点的室友在一个社区大学学会计,属于“成熟学生”。她是川妹子,身躯玲珑,穿起黑色吊带来有一种风情。她又是怎么来到多伦多的?
面对新移民,有两件事不直接问,一是“你怎么移民过来的”,比如我不能问前任房东,没学历,没工作,他是怎么留下来的;二是“你的个人状态”。正常情况下,无外乎“单身”和”已婚“,新移民就有点复杂。已婚了,一个来这里,其实就是”假单身“的状态,很多人倒不是想隐瞒状态骗个约会,虽然这样的人也有,大多数人是因为通街都是陌生人,“我不关心别人,别人也不关心我,既然如此,何必一来就自报家门?” 比如年长的室友可能丈夫在国内赚钱;年轻的室友倒是主动说自己离婚了,但是高大的前夫一直帮她买菜,而她说起前夫来语气里有太多哀怨愤懑的情绪,“我差点从楼上跳下去”之类。除了闺蜜和八卦到无法控制的人,谁会追问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不过住在一起,总会培养起感情。她们越来越不设防,开始跟我说心事,但是她们的话题太遥远了,而我的心境她们也没有共鸣。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因为失眠焦头烂额,并没有心思寻找友谊。当她们把我当作闺蜜一样倾诉,我只能表演倾听,假装关心。但这样是不对的,是浪费自己的时间和她们的真诚。
几个月后,在9月份的时候,学校开学了。忙起来的规律生活让我的失眠渐渐好转,人自然没那么郁闷。是时候搬家了,一定要找到更能谈得来的室友,一个更像“家”的住处。很快,多伦多大学的家庭公寓楼里有了空缺。
一个人时搬家很容易,没家具,国内带过来的两个大箱子一收拾,加几个纸箱,花几十块加币雇辆华人开的面包车,“家”就搬走了。
我的新室友木明也是多大的研究生,大连人,近40岁,圆脸短发,就读教育系。她带着10岁的儿子,住着两室一厅两卫的公寓,为了省一点,就把客房租给了我,她自己住主卧,儿子就睡在客厅的一张床垫上,客厅同时还是饭厅和孩子做作业的地方。她的丈夫在国内上班赚钱。新移民中这种情况太常见了,木明就是“假单亲”妈妈。
本来在分租的环境里,很难有真正做主人的感觉,木明的热情打消了我的许多局促,平时聊天越来越多,偶尔说说心事,大家真的成为朋友。木明很会烧饭,尤其包得一手好饺子,每次都会分我一碗。逢年过节,她叫上几个朋友,大家凑在一起做饭聚餐,就是新移民们最常见的娱乐了。环境简单,亲手做出来的菜式却丰富,室外雪花飘落,室内人气腾腾,热闹中清醒地记得我们都身出异乡,“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油然而生,然而并不太伤感,只有很多“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温暖。
我平时不占用客厅,吃饭也在自己房间里,对着一个14寸的小电视,听上去有点窘,其实那时顶快活。书读的不错,需要用心费脑,但是又不至于压力重重。多谢曾经的外企优薪工作,积蓄小心一点花,可以坚持到毕业,想想明天,后天,下一周......没啥可担心的。当初决定来这里,也不指望是来度假的。对困难的充分预见,往低里压的期望值,是新移民应付初期动荡的不二法门。
木明也做足了心理准备吧,平时挺开朗。多大的教育学院非常出名,她在国内也是做老师的,专业很对口。毕业后慢慢找,找到一份平常而稳定的教师工作是没有悬念的。但她也有脾气失控的时候,引爆点是即将进入青春期的独生儿子。
曾经的福建房东吼娃,这一回,一个中年母亲暴露了她的失控。木明在训斥跟她差不多一样高的儿子时,声音尖利得让人听不明白她在说什么,歇斯底里。骂的无非都是孩子不听话,没做好作业之类。事情说起来普通,不过对于一个新移民单亲母亲来说,也许就是一个倒霉日子里的最后一根稻草。她那在国内兢兢业业赚钱的先生,除了寄生活费,可就啥也帮不上忙了。大人选的道路,孩子只能接受,然而这也不是大人的错,她也有权利过自己想过的生活,至少是尝试一下。更何况很多人出国移民的动机根本是孩子,孩子领不领情,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一年多来,木明的丈夫从国内飞过来探访了母子俩一次。他是一个高大和善的山东人,带着眼镜,职业是远洋海船上的工程师,也是个见过世面的人了。一家三口过了三周颇安乐的日子,就争执过一次,应该是在讨论木明拿到学位后何去何从的问题。她先生要在加拿大找回本行的工作不容易。“专业工作”,就是新移民安定生活的保障。找不到专业工作,对一个中年技术人员来说将是一个生活的巨大转折,比什么“中年危机”的威胁都要大。
果然,毕业后木明选择带着孩子回国和丈夫团聚。她心有遗憾,“就业市场再不好,我慢慢找,从做小学临时工教师开始,总归可以转正,转正后就不愁了。”
“就是为了他回去的。要不是看他是这么好的人,谁回去?”
那个时候我没有决定,毕业后怎么办?那时,移民拿到身份后回流是非常普遍的选择,有些人是因为工作难找,有些人是因为不喜欢加拿大生活,有些人是想赶上国内蓬勃的经济发展黄金时期。正因为许多人回流,甚至不惜放弃身份,木明的犹豫并没有带来太多的震荡。其实,那是一种多大的迁就?
木明毕业了。我提前一天搬到了新租的单身公寓里。那天晚上,小小的公寓里很静很空。到多伦多的近两年里,这是第一次一个人住,感觉从来没有那么自由过,自由到孤单的感觉,让人落下泪来。第二天,我给木明发了个邮件,说想念她母子俩,那是我最后一次跟她联系。
2004年,我拿到了硕士学位。工作市场依然萧条。一个“本地经验”的要求,就把新移民吃得死死的。国内外企的经验并不香,因为“外企儿”太多了,何况街上还满是被本地高科技企业裁掉的人。
一个国内名外企前员工朋友,下了很大决心辞职,到多伦多和妻子团聚。7个月没找到工作,还不如妻子在咖啡店打工能赚到钱。他掉了几十斤,原本精壮的小伙憔悴不堪,顶不住了,趁着原外企招人,回国了。妻子也放弃移民身份,跟回去了。两年后他们却在打听,有没有办法把移民身份搞回来?真是,来来往往,得失之间,都是故事。希望两全,乃人类天性。
更多的人坚决扎根,不少人走上了做“义工”的道路,就是免费干专业工作的活,就为了在简历上加上一行“本地经验”。一些中小企业的老板很会利用这一点,能剥削就剥削一下,连“义工”的位子都竞争激烈。那些移民,不少高薪白领,技术人才,没想过要如此先委屈自己。形势比人强,能屈能伸,把思想搅通了就好。
大批的技术移民去打体力工。工厂,农场,咖啡店,餐馆,都有新移民的面孔。加拿大的劳工保护健全,推崇“职业无贵贱”的理念,体力工者社会地位并不低,收入也有一定保障。可是绝大多数技术移民从没接触过体力工作,这种改变,与其说是体力上的辛苦,不如说是精神上的试炼。
读书期间,我在餐馆短期地打过工,一半好奇,一半想测试一下自己的谋生能力。那是一个受欢迎的越南餐馆,中产的心头好。那些侍应生姑娘小伙穿着烫得笔挺的黑色制服,看上去时髦漂亮,而我是在后面的厨房里炸春卷,拌色拉,烤牛排和大虾。制服不合适的制服和过大的帽子,让人在腾腾热气中面目模糊。
我全力开动自己读书时练就的记忆,死磕制作工序和注意事项,居然把“十指不碰阳春水”的本质掩盖得严严实实,手脚麻利不犯错,没多久就成了熟手。心中有点骄傲,有点安慰,看来适应性不错。除了谋生能力得到肯定之外,我大开眼界。“阶层”这个字眼从来没有如此含义真实饱满,特别是对一个习惯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中国移民来说。
在国内,我不做饭,整天去餐馆,跟无数的服务员说过话,却从没想象过他们在门帘后的日常;雇过几次阿姨,给她们合理报酬,态度友好,但从没有兴趣去了解她们下班后的生活。再怎么尊重体力劳动者,也知道彼此没有真正的交集。甚至不是因为经济条件和教育水平的差异,就是社会为我们本能地划出了一条鸿沟。而在多伦多餐馆里,油烟和各种食物的气味中,这条鸿沟被打破了。下班的时候,当我脱下熏得满是味道的制服,厨房里的两个工人在一旁说,“原来是个秀气妹子。”“什么人穿上那套制服都不好看了。”
依然很难跟餐馆的同事成为朋友。他们大多数是越南移民,没受过高等教育,经历背景迥异,但是和他们在一起工作的短短经历,让我进一步理解了什么叫“人间烟火”。人与人的差别,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优越感是可笑的。
人的适应力比想象中大得多,然而,每个人总有自己偏好的环境,比如,下了班以后,我会到边上多伦多最大的图书馆坐一坐,身心放松,呼吸一下那里的书卷气带来的归属感。这说明,咱还是得找“专业”工作,不可辜负多年的教育和投资。
多大的硕士导师是个从科技行业退下来的高管,有很强的行业背景,人脉广,能够找到实习的项目,几乎所有的“成熟学生”就是冲着找工作的机遇咬牙砸下昂贵的学费。但是机遇这件事情是没有保障的,要不就不叫“机遇”了。
导师帮我和另外两个同学找了一个实习机会,为一个中型的电信供应商做一个网络监管应用。这两个同学一个是电信巨人北电的前员工,白人,在北电触礁后被裁;一个是CBC本科生,加拿大出生的华人,父母来自香港。电信供应商公司里跟我们对接的是一个大陆移民,40多岁,职位是技术总监,这种履历在移民中算是相当亮眼了。照说咱该积极跟他套近乎,可是他看上去有点高冷,不像想跟新移民多接触的样子。不难理解,没有谁一定要照顾同族同乡,而年轻的我也是有一点骄傲的,所以整个过程就是“君子之交,淡淡如水”的画风。
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公司有没有后续工作机会,就是想把项目先做好再说。结果很成功,总监说“远超预期”,让我这个成年学生不禁有“老泪纵横”的激动。
但是没啥用,还是没工作,项目结束后我就离开了,开始在外头找工作,看网上的招聘广告,对着职位要求“吭哧吭哧”改简历,投了20份,除了接到一个电话,一个面试通知也没有。那个唯一的电话成为我求职生涯的耻辱。
事情是这样的。接起电话,一个印度口音极重的声音说,“我是从xxxx打来的,看了你的简历。“
“哪里?“我问。
“就是xxxx。”
依然如听天书,只能又问了一次。然后他说,“对不起,打搅了”,直接挂了电话。
后来回过神来,才猜出他说的是一个著名招聘网站,发音如同鸟语。这折磨人的印度口音,我有待提高的听力和接电话技巧,让一个可能带来工作的机会溜走,留下因为脸发烫的我,和受伤的自尊。
比起不值什么的自尊心,找工作时屡败屡战的“厚脸皮”更重要,我打算尝试流行的找工大法:Cold Call,意即主动出击,要么找到电话号码就打,甚至亲自送上门去,问人要不要招工。这无异于大海捞针,不过总有人告诉你,他们成功了。那为什么不可以是我?
找工作找了一个月,一无所获,正在彷徨之际,原先实习公司的那个高冷华人移民技术总监打来了电话,问我想不想过去面试。第二天我就赶去了,见了招人的直接经理,一个看上去50多岁的白人。他很和气,问了些技术问题,就问预期年薪是多少。
“5万加元”,我说,心里惴惴,是不是开高了?关键时刻,面试和谈判技巧都忘到九霄云外了,应该让对方开价嘛,真傻!
经理想了想,说,“行,就6万吧。”
看来6万是那个职位最低的起薪。到底是大公司,尊重规则,以君子作风讲价,“便宜”了我。开始上班后,新认识的大陆移民员工分享类似的场景,”给的薪水比自己开的高。”我心想,“那是因为你开得低啊,老兄!”
第一份工作就这样尘埃落定。我的“贵人”、那位推荐面试的华人总监后来告诉我,“中国人有机会就要帮助中国人。”
拿到工作后,我立马走进一家路边的机票售卖点,以个人旅行史上最高的票价买了第二天回国的机票,回程是一周后,正式上班前一天。我终于可以花钱了,有了安安心心回家看看的底气了。
有了工作,日子安定下来,时间过得特别快。登陆多伦多转眼三年,我可以入籍了,这意味着移民之路又到了一个分岔口前。许多新移民并没有走到这里,他们早早选择了回流。加拿大的国家统计局数据说明,在过去20年里,有相当数量的移民并没有在加拿大定居下来,“其中,移民时年龄在25至45岁之间的男性移民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最终选择离开加拿大。”
中国内地移民回流的不在少数,首位的回流原因是为了经济和工作发展。找到稳定收入的工作并不容易。移民大多都经历了一个挣扎期,不分种族。有些人从此放弃“专业”工作,改成打体力工,做技术工人,做小生意。比如出租车行业,就是巴基斯坦移民的天下。
有人质问加拿大政府,“你们把那么多有高等教育背景的人移进来,却没有办法提供充足的职位,这不是浪费人力资源吗?”是,也不是。政府为了帮助移民就业,投入了不少资源,比如免费的英文课,众多的就业指导中心,有人帮着改简历,练习面试技巧。但是最主要的“供需平衡”问题是无法靠这些小打小闹解决的。经济差,找工难就是客观规律。即使经济好起来,第一代移民的竞争力一定会打个折扣,比如原先拿手术刀的,移民后离开医疗行业的比比皆是。
朋友中回流的不少。多伦多大学班里成绩最好的同学,曾在国内大外企工作过。他面试成功,找回了老东家一个更高的职务,一毕业就和妻子打道回府了。这一届中国独立移民条件更好,选择更多,也就更容易举棋不定。走不走?归不归?一打开多伦多几个华人聚集的论坛,有专版“回国发展”讨论,满屏都是千般纠结,万种哀怨。有些人,两边观望,做什么选择都“意难平”。
今天再打开论坛,这个板块没有了。加拿大移民部的数据显示,中国大陆向加拿大驻北京大使馆申请技术移民的人数,自2002年起呈减少趋势。这几年,“回国发展”不再是个主要话题。想回的都回了,留下来的都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人生的无限可能性消减了大半。但是十多年前,两难的境地很真实。其实,世上又怎么会有完美的选择?我们总是什么都想要。
2007年,来到加拿大第4年后,我裸辞,跟朋友们吃了散伙饭,一个人拖着两只大箱子,回到了广州。
辞职前,我跟介绍我进公司的华人总监喝了杯咖啡。身为师长,他想给我一点建议。在有点拘谨的气氛中,他说,“你回去后可能会发现,有些事情已经不一样了。”我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我们还没有熟到可以说心事的地方,我也没打算想跟任何一个人详述选择回国的心路历程。
咖啡喝完,我们各自回办公室。他最后说了一句话,“你会发现,人生很短。”我无力反驳。有些时间必须被浪费掉。我必须给我的婚姻一次机会。
移民是我的主意,周林一开始没坚持跟我一起来,我也就不勉强。是不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心里已经做好要放弃这段关系的准备?我不知道。或许没有那么轻易放弃吧,要不我怎么会在彼邦的生活安顿下来以后,再次连根拔起,回到广州?我要伤筋动骨地越洋搬家,重新找工作,重新融入生活,这些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周林呢?除了同意我把他的名字加到移民申请里,他从来没有真正为移民做出任何努力。他没有花时间提高英语水平,没有认真研究过多伦多的就业市场。他在广州努力创业,如鱼得水,赚钱虽不多,能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生活负担也不重。我一定要他移民,他应该会来,可他能熬过开始的艰难吗?他会开心吗?如果他在很长时间内都无法自立,必须依靠我,我会高兴吗?两个人的压力都会很大吧,我并不是什么“女汉子”,能背得起自己,背不起两个人。
两个人都在犹豫中等待对方主导事情的发展。想来想去,那我回去好了,如果我们还想在一起。多年以后我才能真正面对自己的内心。我这么做,是为了让自己的良心好过些吧。因为自己是离开的一方,一直有种亏欠感,所以不能做主动放弃的一方。
我回到广州,周林很高兴,很感激,生活里一如既往地体贴。我去了,我来了,好像是一件云淡风轻的事情。生活看上去几乎跟移民前没啥不同,除了工作。我以“海归”背景,仓促地找了一份在创业小公司的职位,头衔不错,收入尚可,工作环境就比在外企时差远了。那时,广州外企的合适职位也不多。深圳华为倒是有合适的职位,但是我万里归来,难道不是为了和周林生活在一个城市里?
两人都忙工作,都不做饭,常在外面吃,周末到公婆家里聚会,节假日安排一场旅游。好像一场移民从来都没发生过,假装我们没有分隔大洋两端三年之久,假装我们还是一对好夫妻。可是,生活真的能跟原来一样吗?事实却是交流越来越少,对将来不再有憧憬,连生孩子也没计划。
回来一年后,我一天比一天想逃离这个城市,逃离忙乱不堪的工作,逃离一段如潭水般静寂的关系,逃离热闹烦杂的圈子。我提出了离婚分手,理由是我想回加拿大。是,又是我主动。忘了我们都说了什么,只记得周林哭了,我也哭了,满心都是失去亲人的痛苦,和对将来的惶恐。双方的父母都没有试图影响我们的决定,只是表达了善意的失望。每个有经验的人都能看出来,我们心意已决,只能分道扬镳。
不能说浪费了这一年,有些教训,必须亲身下场挨打才能刻骨铭心。我和周林都不是决断力很强的人,但都是“好人”,而这两样品质组合起来,常常让事情变得复杂。我回流,只是形式上做到了,心是飘忽的,并没有下决心好好过日子,修复我们的关系;他欢迎我的回归,却没有做出额外的努力,让我相信回来是值得的。
2009年,回中国两年后,我再次起程,又拖着两个大箱子,来到了多伦多。这次是真的一个人了。
同样的程序再来一次,找地方住,找工作,重新跟朋友们联系起来,又见美丽的枫叶和皑皑白雪。一切都容易一点,我讪讪地笑自己,毕竟第二回了,有经验了,不再是新移民了。
很快,我加入了加拿大国籍,后来结婚生子,过着过着就成了老移民。周林比我晚一点再婚,一直没孩子。据家人说他工作愉快,时常跟朋友们一起吃喝旅游。因为要处理在广州的户口,我们后来见过面,很礼貌,不过没有保持日常联系的打算。“至亲至疏夫妻”,这话一点儿没错。不那么强壮的关系,最终总要让路于两个人方向各异的人生追求。
回到一切的起点,为什么移民?有些理由似乎显而易见,比如,为了发达国家的安定生活和健全的社会福利,为了孩子将来的教育和发展。随着这些年国内的变化,理由或许又换了一茬,或许已经没有理由。那也是一种进步。
这些年,我被生活裹挟着往前走,没深想过属于自己的答案。直到最近两年才回过神来,其实那些别人都在说的原因,没说到我的点子上。如果对自己足够坦诚,我得说,一个年轻人必须为冲动负上责任。她极好奇,想看看异国究竟有什么不同;她有点跟风,既然那么多人去了,这怕不是坏事?她并不志在必得,如果移民加拿大需要努力折腾的话,大概率就不干了。
感谢时代给我的选择。其实我不算最适合的移民“材料”。都说中华文化情结太重的人出国后不容易过得好,自己偏偏就是一个这样的人:热爱中文,喜欢唐诗宋词;长着一个中国胃口,曾经连个汉堡包都食不下咽;跟家人朋友很痴缠,每年必回国探亲,每回离开时都舍不得至痛哭流泪。那种在机场登机的冷寂空虚,不足为外人道。
很多年了,即使在有了一个安定的家以后,心中的故乡依然在万里之遥,而此地是异乡。第一代移民的身心痛苦,我肯定是尝到了自己应分担的份额。回望来时路,知道移民总是为了整体更好的生活,不管是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结果是否如愿?付出的代价值不值得?
这个问题,在移民17年以后,有了答案:这是合适我的选择。开放的加拿大,多元的多伦多,和愿意学习的我,合在一起,像一场包办婚姻,我们糊里糊涂先洞房,再慢慢谈恋爱,现在看来会长长久久;不仅仅是习惯,更是契合,让他乡,成了第二个故乡。
那个磨合过程,是另外一个故事。
现在,纵然还有苍茫的时刻,我终于能说,“此心安处是吾乡”。
原标题:《17年前,我和近3万中国移民一起登陆加拿大 | 三明治》